李慈湄、郭家穎「『啟.靈』:西洛賽賓(psilocybin)之耳⸺聆聽心靈」這項計畫,以近年來在精神醫學領域備受矚目的「啟靈藥」(psychedelic)輔助心理治療的作為為引,探索電子音樂在心理治療上的療效。計畫名稱「西洛賽賓」即「啟靈藥」藥名音譯。
「啟靈藥」是英國精神科醫師漢弗瑞.奧斯蒙(Humphry OSMOND)在1956年創造的字詞,指具意識轉變效果的化學物質。Psychedelic由兩個希臘文字源組合而成:psyche意指心靈、心智,delic意指顯現、呈現。過去多將psychedelic翻譯為「致幻劑」,近來則有「啟靈藥」的譯法,更為貼近原字詞「啟示心靈」、「顯現心靈」的意涵。近十年,運用啟靈藥治療精神疾病的人體臨床試驗研究已累積出令人驚豔的成果。1
大學就讀心理系的聲音創作者李慈湄與精神科醫師郭家穎,兩人的共通之處有二:一是他們大學時就參與社會運動、關注社會議題,準確地說,是自2004年起的樂生運動,以及近年許多反抗運動中的文化行動。第二是他們都喜歡電子音樂,同時也是聲音創作者、DJ。2011年福島核災後,臺灣「非核家園」運動正興,他們與一些電子音樂同好主張「電音反核」的運動方法⸺以2013年成立「P.L.U.R.S.電音反核陣線」2作為正式的「電音反核」團體。在本次訪談中,我們從2003、2013年這兩個時間點開始談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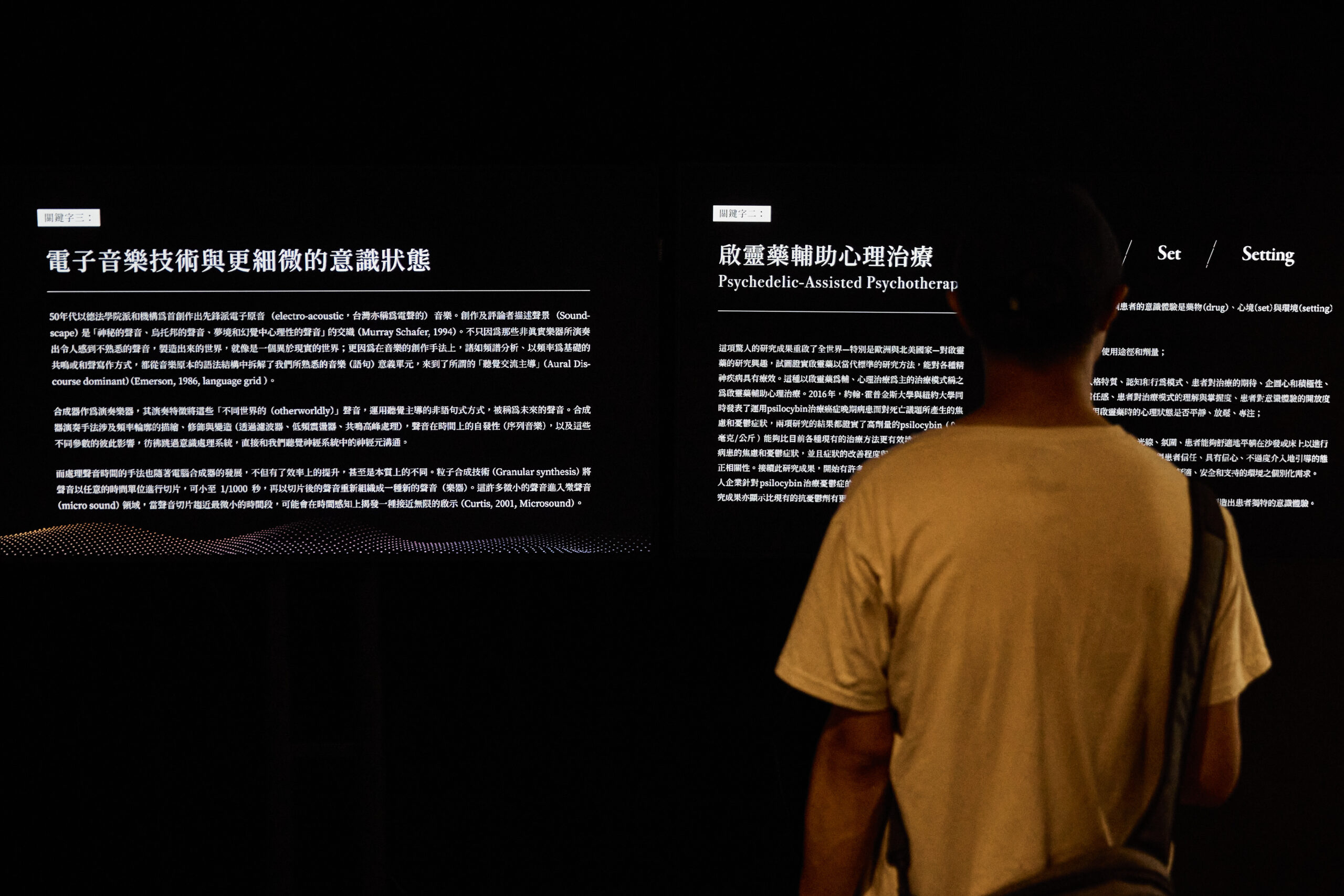 「『啟.靈』:西洛賽賓(psilocybin)之耳⸺聆聽心靈」開放工作室。圖/陳又維攝影。
「『啟.靈』:西洛賽賓(psilocybin)之耳⸺聆聽心靈」開放工作室。圖/陳又維攝影。
葉杏柔:音樂的光譜之廣,為什麼是以電子音樂進行反核,以至今日藉電子音樂「啟靈」?你們相識於「電音反核」的行動大概是哪一年的事情?當時兩個人如何在自己本來的工作(或作為學生的主修科系)領域關注、參與反核以及其他社會議題?
李慈湄:就讀輔大心理系大三、大四時,因為系上田野課的關係,我陸續參與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1999年成立)的活動「國際娼妓文化節」,也接觸都市原住民相關的議題和社區空間,以及TIFA台灣國際家庭互助協會(1996年成立)等。那時大約是2003、2004年。我在大學的時候患有恐慌症,不常去學校,反而持續投入因田野課加入的NGO。畢業後,我更積極參與關注整體政治社會議題的人民火大行動聯盟3。在這些NGO裡,我經常在帶藝術創作工作坊的過程中與社會底層群體相處,這些經驗讓我發現藝術活動對人們具有很大的賦權(empower)力量。
葉杏柔:時間、地點剛好接近樂生運動。
郭家穎:對,樂生運動從我就讀大學二年級時的寒假開始(2004年2月「青年樂生聯盟」成立),在2008年底遭強拆之後告一段落。當時我就讀陽明大學醫學系,我開始參與的時候是2005年暑假的「音樂.生命.大樹下」音樂行動,那時候大三升大四。運動大致分為「捍衛樂生院民人權權益」與「爭取舊院區指定為文化古蹟」兩個軸線,2007年9月之後,我和我太太兩人開始進行漢生病口述史工作。那個時候非常多人聚集在樂生療養院;那是一個十分罕見、作為聲援者要做什麼聲援工作,基本上都可以的場合。有非常多人去拍紀錄片,也有人去幫流浪動物結紮。不像大多數的社會議題──譬如楊儒門2003至2004年間的「白米炸彈客」事件⸺即使聲援者可以聚集於中央部會示威,但整個抗爭過程沒有一個聲援者經常能夠聚集的場合。而樂生就是這樣的所在,是一個很開放的抗爭基地。如今回頭看,樂生經驗給我們的寶貴遺產,就是一個「去大台」的社運雛型,而我跟慈湄都很認同這樣的運動方式。電音本身具有去除傳統演出「表演者—觀眾」這種單向注視關係的特質,這讓觀眾有更多彼此相識的機會,而我們認為這很重要。在其中,參與者是更有主體性的,不會只被限縮在台上台下的關係,而是可以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2009到2010年左右,樂生青年、野草莓運動4參與者聚在台北公館的直走咖啡。5那個時候已經有不少樂生青年從事NGO工作,例如綠色公民行動聯盟,我則是開始在臺大醫院精神科工作。也差不多在這段時間,臺北放電子音樂的場合越來越多,譬如Pipe、Revolver、Korner等,也有更多戶外派對,我因而認識電音,以及相同理念的朋友。舉例來說,目前任職於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的陳詩婷,就是我在2010年元旦福和橋下的電音派對認識的。記憶中她穿「苦勞網」T-shirt,又站在票口,我們就聊了起來。同時聚集在直走咖啡的運動者,包括楊子瑄、洪申翰這些人,也一起辦了「諾努客走唱隊」,將運動和文化結合在一起。2011年日本發生福島核災,臺灣的反核運動白熱化,我們幾個朋友組合起來弄一台「電音卡車」,以播放電音的方式參與街頭遊行。自2011年開始,社會運動累積了幾年的集結能量,反核運動在2013年的核四公投達到高峰,然後在2014年的三一八運動將這些能量一次爆發殆盡。當時我在臺大醫院也就近支援。我們這一夥樂青、野草莓運動者、TIWA台灣國際勞工協會成員等等,一起在濟南路臺大校友會館前方搞出一個「賤民解放區」6,每天舉辦「公廁旁解放論壇」,有時也會放電子音樂。一開始其實就只是拿著小型的擴音器材放聲音、有些人敲水桶,在當時議場內外還沒有秩序,是一個群眾佔領公共空間的狀態,類似國外TAZ (Temporary Autonomous Zone)的概念。
蘇唯瑄:《於是我們歌唱》是一部拍攝「諾努客走唱隊」的紀錄片,在紀錄片今年的映後座談中,陳詩婷談論「電音反核」的發想時,曾經提及希望以電音作為一種表達形式,以及串連運動中的身體感。不論是在社運現場,或是在用藥經驗中,電子音樂似乎都扮演了一種通道的角色,橋接日常與非日常的空間和經驗,而電子音樂創造出的異質空間,又與它激發出的身體感受息息相關。想請慈湄分享更多進入社運與電子音樂場景的契機,以及兩位對「啟.靈」計畫的發想,是否延續了各自在社運與電音場域中的實踐,以及其中對於空間的思考?
李慈湄:我大學的時候很快就進入社運,同時也玩樂團。但我很快就發現臺灣的地下樂團生態具有強烈的陽剛主導性,我在裡面很難找到自己的角色定位。與此同時,我也很快對非具象的樂器聲響產生興趣。大概在2000到2010年,後搖滾在臺灣蓬勃開展,它打破了以往由大敘事主導的旋律樣式,呈現出一種以不同敘事共同編織出的音景,這也符合當時大眾意識形態的轉變。後搖滾當中引入了很多電子音樂的聲音,因此我其實是從聲響開始進入電子音樂,而非跳舞場景。在電音反核的角色上,我也比較是被家穎、詩婷組織進入派對文化,同時也在裡頭找到文化與社會關懷更多的實踐可能。
回到社運上,我接觸的左派階級運動跟家穎談到的樂生不同,比較是由上往下、相信社會大眾是要被教育要被啟蒙的。比較正面地說,是對社會有改造的責任,但同時也會有比較負面的傲慢產生,而這個傲慢的根據可能來自年齡、性別或是知識,種種權力階層於焉產生。我是很不能進入這種文化的,反而是在電音裡面找到和社運不同的那一面、找到我自己相信的價值。
不過,即便當時的運動者受剛才提到的多元或去中心的精神吸引,但是電音文化也沒有那麼快就進入社運群體中。對社運人來說,參加集體行動需要有明確抵抗的對象,比較難想像自己受到了音樂吸引,就大家聚在一起跳舞。我們當時找了一些過渡的方法,比如說在「奪回公共空間」的號召下,半夜去松菸誠品辦了幾次派對,讓大家擊鼓、砸可樂罐,製造一些節奏,思考可以在公共空間做什麼。
如果以音樂類型做例子,其實當時大部分運動的形式都還是樂團式的場合,但我們想像的運動形式應該是更自主的、電音式的場合。以這點而言,樂生是一個滿特別的社會運動,各行各業的工作者或學生,只要有興趣就可以參加,就算沒有加入組織都可以找到空間去做計畫。也許在運動史上,樂生的抗爭無法被認定為成功,但我認為它對臺灣後續至少十年間的社會運動文化和風氣影響很大。當時的樂青或者非核心的樂生運動參與者,後來都在不同的場域找到其他實踐空間。如果以C-LAB的定位來比較,那時的樂生可以算是一個社運文化工作的培養皿。很多組織工作者在樂生的時期拿起了攝影機,開始做一些文化工作。而文化工作者可能開始培養自己的組織意識。
三一八的時候,過去醞釀的很多議題開始被討論,像是不要大台,或甚至是性別分工的問題,例如當時所謂的太陽花女神。不要大台其實就是自己要更自主,但我們過往不管是接受教育或是各種行動的形式,其實都在剝奪我們的自主性,所以一下子也真的不知道怎麼自主。反而是香港反送中展現了非常令人驚訝的模式,大家各有各的分工、各有各的群組。我過去一直在做組織跟抗爭的工作,但我在裡面其實沒辦法找到符合自己相信價值的實踐位置。我和家穎關心的是去中心化或者自力組織的方式,當三一八結束、社會抗爭的能量消耗得差不多以後,反而我們因為有前面的經驗,得以一方面創作,另一方面思考如何不是用偏向搖滾樂而是電子音樂的方式,進行與社會相關的文化行動。
郭家穎:我是2009年開始聽電音,隔年開始當住院醫師,2010年剛好也是臺灣電音場景的復興。臺灣電音場景第一波是1994、1995年,《破報》剛創刊,從《立報》獨立出來的時期,DJ @llen辦了一些rave party,舞廳開始成立,高峰一直到2000年。7但後來因為黑道介入和藥物販售的問題,舞廳陸續被抄掉,包括最知名的teXound,還有2nd FLOOR都在2004年關了,比較知名的只剩Luxy。一直到2010年才開始有一些場地出現,包括前面提到的Pipe、Revolver和後來的Korner,PsyTrance曲風的音樂團體也重新開始在戶外辦派對。這一波復興提供電子音樂表演的機會和空間,也比較穩紮穩打,不像第一波大眾參與的狂潮,同時音樂組織也慢慢形成,像是Smoke Machine、Bass Kitchen等。我在工作的過程裡繼續參與到電音的場景中,中間有穿插反核遊行的時期。我認為現場是很重要的,沒有空間、沒有現場,文化沒有辦法繼續發展。有空間出現、有表演可以發生、有人可以聚集,文化才有辦法復興。
葉杏柔:慈湄曾經提過,人的理念會影響行動,終而形塑出屬於他/她個人的物質基礎。從「起心動念」到「行動」整個過程也是本計畫關注的焦點,音樂在這個層面上像是意識的測繪。
回到你們相遇的原點,社會運動蘊含著如何完善福利制度、人權條件等高度「行動主義」的內在動力,是個人行動沒錯,但必須透過群眾才能實踐,這涉及到集體的共識、記憶。在剛剛家穎的描述中,樂生經驗、電子音樂兩者都是「現場、多人、去大台」,而「啟.靈」計畫要給公眾的是如何在「隨時隨地、單獨、關照自我」的條件下「顯示心靈」。請談談電子音樂的「啟靈」作用於私我療癒,還是集體的情動(affect)?
郭家穎:2011年,在我們第一次以電音卡車參與社會運動那陣子,有一項重要的醫學進展,是美國的非營利組織MAPS(Multidisciplinary Association for Psychedelic Studies)於2010年以MDMA輔助PTSD心理治療的第二期臨床試驗研究(我在2012年讀到這篇研究)。8這讓我開始持續追蹤國外啟靈藥物輔助心理治療的臨床研究。而在去年,我讀到一些文獻資料,指出音樂在治療療程中的重要性,我才進一步聯想電子音樂與啟靈效果。
至於是私我還是集體,我比較會從這個角度來想:電音派對的集體性、去中心特點如何與現實結合?我想的是有沒有可能發展音樂在心理治療上的功能,找出精神醫學、藥物與音樂三者的結合,以及達成啟靈藥物輔助性治療的效果,甚至結合日常生活的可能。譬如若病患身心狀況不好的時候,可以自行聆聽特定的電子音樂得到療癒效果。至於能不能達到集體的效益,我覺得要再思考與設計體驗形式。
李慈湄:物理上的限制確實是我們這十幾年來做電子音樂一直遇到的,很多人嘗試比較直接的克服方法就是找到空間,不管像是前面提到的直走咖啡,或是後來的半路咖啡。以音樂的表現性來說,要有空間,還要有相稱的聲音系統。甚至,現實的限制在於,聲音系統是臺灣無論娛樂影視或藝文的製作中,最容易被犧牲或忽略的。做聲音創作就是這麼受限的情況。
這裡頭的反思有一部分來自我在左派運動的經驗。我想臺灣的左派運動若有失敗的部分,有許多運動者必須為這些失敗、這些誤解負責:我們常有一個很大的邏輯錯誤,就是把批判對象視為他者,認為自己不在(問題)裡面。第二個邏輯錯誤,是手段和目的互相矛盾。帶著這樣的反思,我會覺得現實上可以放音樂的條件越來越少,其實也就是公共空間變得越來越小、越來越少,那我們自己在其中的責任是什麼?我們這幾年來做了哪些決定導致這樣的結果?十幾年以前,臺灣社會運動的場域條件確實讓運動工作者與文化工作者兩邊可以很好地合作,但近十幾年來不是如此。而公共空間被吞噬的這些歲月裡,我們的意識產生多少改變?這是我十分關注的事情。我相信若這個狀況可以被更多人意識到,可以被討論甚至產生改變,也許我們會因此更在意我們所處的環境。我希望做出的改變,比較接近你說的集體的情動。
蘇唯瑄:在你們的談論裡,我一直感受到社運和電音具有某種空間的性質。如同家穎曾經在一場講座中提到「場」的概念,不論是電音派對去中心的舞台會營造出一個去中心的場,或是在英國的街頭以電音形式抗爭的運動者。你說他們並非把派對搬到街頭,而是那些人本來就是電音文化的實踐者,這個街頭抗爭的場景也是電音文化實踐的一部分。我開始有一種想像,會不會這個計畫也是你們的一種文化實踐,它除了是一個心理實驗和聲響實驗之外,也是基於你們對臺灣的社運、電音文化甚至醫療現況做出的抵抗?我突然有一個抽象的想法,會不會就是在這樣的現況下,追求一種更自由的狀態?
李慈湄:講更自由我其實滿認同的。我覺得更自由了,是因為我更知道電音、社運、音樂和意識是怎麼一回事。但同時我也在想,我想像的自由是什麼? 自由聽起來很個人,但它其實是很集體的事情。單單以臺灣這個環境來說,如果我個人極度地自由,但身邊的人都很不自由,像是被很多信念所限制,那我可能也自由不到哪裡去。我覺得自由也是一個互動的結果,而且是一個共同擁有的狀態,我好像是在追求那種共有的自由。
蘇唯瑄:我也注意到,你們兩位在計畫中都涉及不同的身分,不同身分的聲音不時會交錯。比如對家穎來說,從醫師的角度,這個計畫在心理治療的實踐可以是一種讓電音的特性被落實在現實的方法,而同時當你談論計畫的其他部分,你會非常在意聲音的質地,這裡參雜了你自己作為DJ的角色。而慈湄可能會是以聲音創作者的身分在研究聲響如何形塑意識、空間感的改變,以及技術層面的問題。
郭家穎:我們很多時候會標籤人的身分,現在常常有「斜槓」的說法,但我不那麼喜歡用斜槓去解釋人的身分,因為斜槓其實意味著切割劃分一個人的身分或能力。以我個人實踐的狀態來說,我是把很多不同的身分連結,是把斜槓(/)變成連接號(dash,-)。我做醫師、DJ、音樂聆聽者,它們其實是會有連動、互動,不會說我在醫師的角度,就完全把音樂切割掉。
所以我又想到你在前面提到的反抗。在精神醫學的臨床工作上,現在的治療基本上是以藥物治療為主,但第一個它成效有限,第二它沒有辦法真正讓人從現實中的壓力或限制當中解放。藥物很多時候只能舒緩症狀、讓受損的神經修復,但大概就僅止於此。所以當啟靈藥的研究被導入精神醫學領域的研究和實作,其實就是企圖讓人突破既有的窠臼,無論是人格特質、思考和行為模式等等的框架。啟靈藥開啟了更多的可能性和自由,透過類似神秘體驗去發現不同的思考和行為的可能性與發展空間 ,創造一種突破現實困境的機會 。
要能夠去突破限制,或者像慈湄剛才提到尋找自由的話,啟靈藥就具有這種特性。當我們在治療情境中給患者使用啟靈藥,音樂和藥物的混合會產生意識的素材,當下的經驗會很深刻地留下來。在他們重新聆聽這段音樂的時候,會回想起當時的感受、想起自己可以怎麼做,音樂也可以是一種治療的工具。另外一方面,目前的健保制度其實會限縮醫師與患者相處的時間,無法更深入談論患者的心理狀態或者社會處境,所謂的啟靈藥輔助性治療,重點還是放在心理治療,希望能更深入去挖掘並討論內在的狀態,才更能夠真正有效地使人從困境中解脫。否則速食的藥物使用只是讓人維持基本的身心功能,但它並不一定有辦法解決問題 。
葉杏柔:這個計畫將大量指涉受訪者在個人經驗、個人記憶中,對於音樂與感知質變的描述,涉及高度差異化的、個人的後設詮釋。兩位進行訪問、揀選受訪者提供的經驗描述,最終要提煉出具啟靈效果的電音形式(pattern)並建構大眾可近用的音樂資源,這本身包含了「質性研究」與「社會服務」兩大工程。在目前已進行的訪談經驗中,兩位如何想像這個計畫在今年呈現時的主要方式?也就是,如何向大眾「發聲」你們的階段性成果?
李慈湄:我們在期末(2023年11月)會以集體音樂會的形式呈現。但音樂要如何與參與者交流,是我們這幾個月要透過訪談、測試之後再討論定案的。呈現的另一部分,則是我們研究文獻過程中的知識整理與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