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劇場死了!」1在九〇年代初出現的這句話,給八〇年代中期出現的小劇場運動下了個註腳,似乎只有這句話才能讓小劇場的歷史討論轉個彎,繞到另一條思考與體制共構的生產關係上。也就是說,歷史不介意路徑如何,但拒絕小劇場運動在言說上被空洞化,尤其在「八〇年代」至今儼然成為一個當代文化研究的關鍵詞時⸺表面看起來是一個可敬的名詞,然而是誰將這段歷史給出所謂「可敬」的定論呢?
在這樣結論下的小劇場運動,其中卻讓我們看到左翼言說的不在,而使所謂「運動」的意義變得晦澀,並顯示出八〇年代左翼的思想脈絡被有意或無意地忽略,至少在小劇場運動是這樣。彼時,受反共主義意識形態支配的戒嚴令先於1987年結束,緊隨之後1991年蘇聯共產政權的崩解,列寧雕像的倒下,全球似乎跨進了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說的「歷史終結論」時代,左翼在此時彷彿成為了「文明的敵人」。弔詭的是,與小劇場運動應運而生喊出「顛覆」此等激進的口號,其實在當時也是一種具有左翼意味的新興文化,譬如在大學校園裡各種新左翼的讀書會,解嚴後亦如雨後春筍紛紛成立。
在歷史這般新的轉進與現實政治之間,新左翼並沒有創造出一個對烏托邦理想世界的想像,或試問是什麼樣的想像使其失去一種力量?我們看到戒嚴的反共遺緒,流轉於共同體受到威脅之存在的東西,那就是隨著本土化路線的現實政治,而將戒嚴下的反共主義置換為抗中保臺的認同政治。小劇場作為文化裝置,隨1987年解嚴,進入九〇年代之後,在國家逐漸建立一套金字塔式、從中央到地方的收編機制下,左右二元對立的結構暫時消失,「文明的敵人」似乎被醞釀成為受另一個來自於大陸文明威脅的統獨衝突。
小劇場運動就在九〇年代以後,突然失去了解釋現實的能力;「小劇場死了!」這句話也是在指涉這個原因。在筆者出版的《都市劇場與身體》(1990)一書,其中的〈台灣「政治劇場」的神話與現實〉一文有這樣的話:「解嚴以後興起的小劇場運動,是建立在自覺的基礎上,而不是在政治主張的提出;自覺意識通過身體感覺表現出與體制對決的姿態,卻沒有表現出台灣人民從歷史制約中解放出來的主體意識。」2此處提出所謂「歷史制約」的問題,即是對於六〇年代「右翼國家主義劇」的反共教育,已經融合進入臺灣社會階層的文化經驗,所做出的根本性批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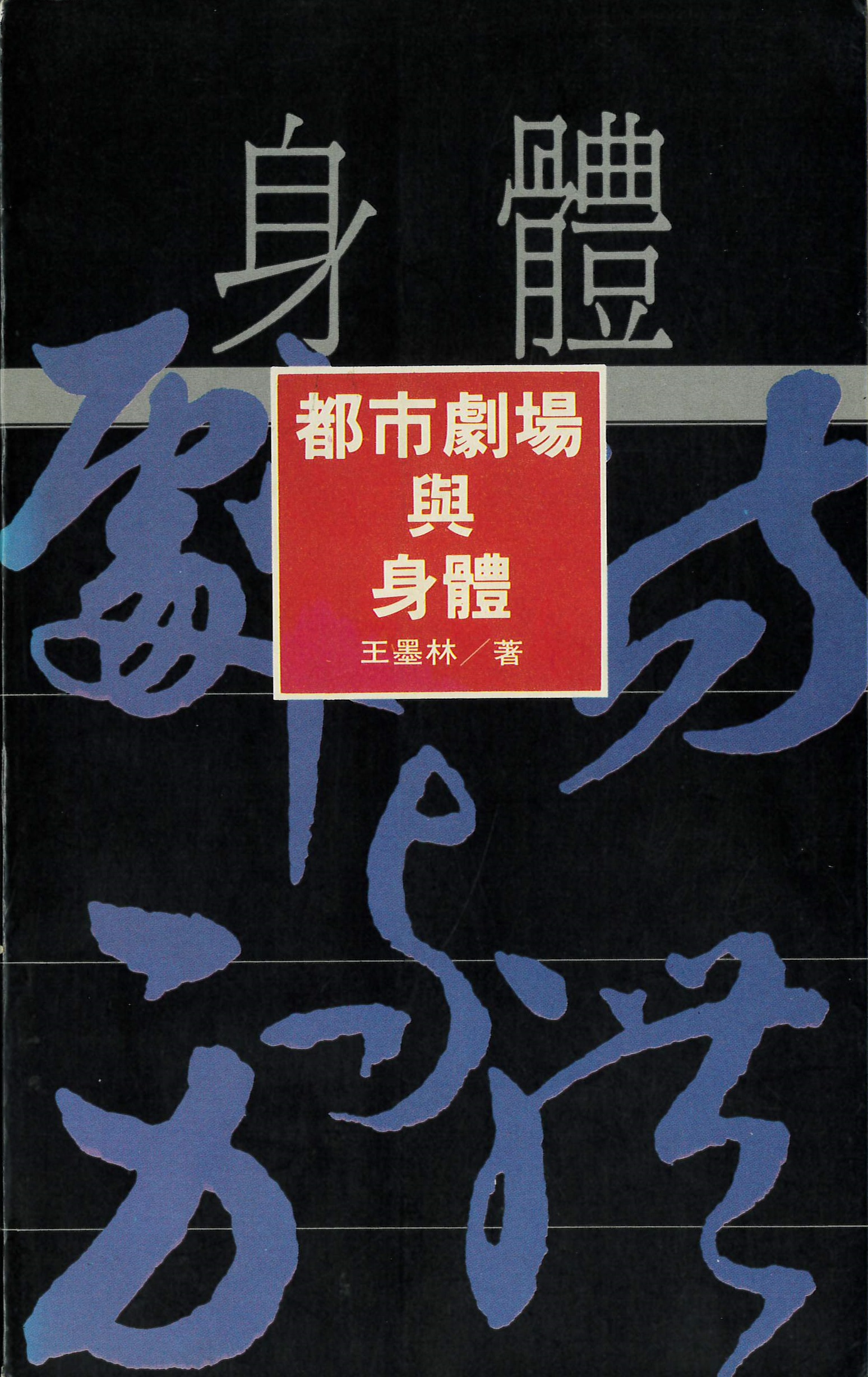 王墨林,1990,《都市劇場與身體》書籍封面,稻鄉出版。
王墨林,1990,《都市劇場與身體》書籍封面,稻鄉出版。
所以,我們要問的是:當戒嚴與冷戰相繼結束之後,二元對立的結構是否就消失了?反而是剝奪了左右議論的現實基礎。該文也對此提出這樣的看法:「戒嚴四十年使政治語言消失在被剝奪的現實批判之中,解嚴後雖已復甦,又變成社會抗議的政治標語,隨著消費意識的日益膨脹更擴大成為政治感性的圖式。」3此文於1989年完成,俟至200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之後,我們就看到新自由主義於焉在臺灣落地生根,使文化創意產業得以陸續發展起來,小劇場又在其中扮演著更為「產業化」的先鋒角色。筆者於上同文預先總結「小劇場死了」:八〇年代為九〇年代棄絕了對立的、社會的政治領域,轉而建構出一種內在導向、自我陶醉的「自戀文化」脈絡,進而形成新自由主義發展的基盤。故,該文在結論時提出:「因意識形態沒有從近代史冷戰結構中解放出來,終歸小劇場的自覺意識還是落在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舊窠。」4
不管歷史要以怎樣的面貌展示給我們看,即使表面看起來可以是無意義或晦澀的,但仍然需要有一個意義,否則將永遠令人懷疑它與自己的關係。因而,我們置身於這個世界,如同正處於自身的歷史情境之中,它提供了我們一起面對的一個相同的歷史情境,至少為一個共同體的想像提供可能性。因此,我們試問:誰是這個想像共同體的提供者(producer)?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曾在《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1983)一書中,以「文化人造物」(cultural artefacts)說明民族主義的本身,而又是怎樣的「想像」(imagined-ness)作為媒介,構築了我們堅信的共同體?
八〇年代小劇場運動的能量,強調的是顛覆體制的行動力;個體想像的是以自己的身體與共同體對抗的個人,行動的獨自性不是異己的虛無主義,也不是孤立的對共同體的背離。當下,郭亮廷在他的博士論文中,也提出對共同體的「想像」的意義追問5 ,其背景更在於2017年民主進步黨執政通過「促進轉型正義」相關條例之後,小劇場被給予贊助的文化機構鼓勵,開始競相製作、演出所謂的「白恐戲」(「白色恐怖戲劇」之略稱)。原本紅色意味的左翼社會主義革命,相對於白色意味的是國民黨右翼政權,使「白恐戲」中這種在冷戰戒嚴期間對島上共產黨活動的鎮壓,續延至今改以「轉型正義」之名、換用新的國家意識,對抗國民黨所代表的右翼政權對左翼活動鎮壓的不正義。也就是說,「白恐戲」的主要目的是邀請群眾,進入劇場即看見「歷史」。若問為什麼「白恐戲」會在小劇場爆發,借用安德森對於「想像」作為媒介的討論,就不如問:是什麼樣的新想像,成為討論歷史與小劇場的新媒介?
其實,即使舊政權曾對左翼活動進行白色恐怖的不正義,至今新政權已以「轉型正義」之名令其受害者獲得平反;但,這依然不是一般臺灣人樂於對社會主義臺灣所假想的幻境,也就是不可能把社會主義的一切優點投射在現實政治上,正因為冷戰戒嚴下的「反共主義」概念模式,已被穩穩地生根在臺灣意識之中。白恐戲作為臺灣「轉型正義」的一環,跟戰後德國去納粹化的「轉型正義」不盡相同,但其中相近的是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在《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1963)中所點出的:「為了人民的利益,只有冷酷強硬才能解決問題,才能保障國家的長治久安。」6
既然「轉型正義」不過是一個「文化人造物」的新名詞,首先出現於新政權,而不是在舊政權時代,其目的或如安德森所言:「沒有一個革命家曾夢想要保持帝國原封不動,他們所夢想的只是要重新安排帝國內部的權力分配。」7。那麼,我們就被分派必須完成做一個「新臺灣人」,學習再敘述這段特定的歷史,以從敘述之中清楚辨識認同。因為歷史的疏隔仍存在對冷戰戒嚴的無法超越,所以通過這樣敘述的認同,只能在「記憶」與「遺忘」之間來回擺盪,標示了歷史和現實生活之間有一個深刻斷裂。這就讓我們更為清晰地看見當前政權在「轉型正義」的政治召喚(vocation)下,「白恐戲」其實只能為新舊政權之間,劃出一個可以識別的分際線,遂使當下小劇場在政府充分資金的支持下,進入了一個文化生產的昂揚期。
進一步我們要試問:在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的歷史中,國家殺人這件事,或者應改正為國民黨右翼政權暴力殺害左翼社會主義者這件事,到底是一樁集體罪行,或個人罪責?漢娜.鄂蘭綜觀納粹高官艾希曼(Adolf EICHMANN)在紐倫堡大審(Nuremberg Trials)的實況,在上書最末這樣寫道:「政治責任跟集體中的個人行為不同,既不能從道德的角度進行評判,也沒有辦法訴諸法庭審判。所有的政府都要為前任政府的政績以及罪行承擔責任,所有民族也都要為該民族的過去負責。」8至此,我們反身思及「轉型正義」何以走到今天左不左、右不右的尷尬地步,不就是其政策只為傳達新政權的正確性嗎?並以此宣揚掌握到歷史話語權的政治立場,導致民眾根本無法得知「白色恐怖」的真實情況,從而隱藏社會的貧富矛盾與階級對立。我們的「白恐戲」看如做到讓一段黑暗的臺灣史重見天日,但左翼於歷史中的存在,仍然像是鏡花中的水月。
 窮劇場X江之翠劇場,2023,《感謝公主》彩排攝影。圖/林育全攝影,窮劇場提供
窮劇場X江之翠劇場,2023,《感謝公主》彩排攝影。圖/林育全攝影,窮劇場提供
我們對於「白恐戲」的爭議,其中要點即在於:如何能夠釐清歷史與戲劇之間的關係?若以「轉型正義」為例,左翼社會主義的革命者是時代敘事的關鍵詞,尤其革命者將建立社會烏托邦與個體獻身作為一種生命抱負;相對於單純的民主加福利國家體制的支持者,似乎就無法與其神聖性相比擬。因此之故,革命者在地下活動即使面臨的是失敗,也可能成為更宏大的敘事素材。去年適巧有一齣《感謝公主》(窮劇場X江之翠劇場,2023),被評論為與眾不同的「白恐戲」,並獲得時下(小)劇場最高獎賞的「台新藝術獎年度大獎」。我們即發現其故事跟「轉向」所意味的信仰喪失有關,更吸引人的是告密者同時也是反抗者所呈現的雙重身分;此乃在白色恐怖腥風血雨的籠罩下,告密左翼同志被當局獎勵,而遭到逮捕的地下黨員則要被當局虐殺⸺這種道德分立論讓《感謝公主》的編導在劇中創造出了一個正邪同體的主人公。
「轉向」在這齣戲裡所意味的信仰喪失,毫無疑問也是作為左翼社會主義者另一種對共同體忠誠的背叛;然而,《感謝公主》最可議的是把作為劇中主人公的「老鄭」,換置為一個不但無能力辨是非、且無責任識實務的虛無者,他如是說:
「老鄭」對自己身為告密者,能夠如此雲淡風輕地對待也就罷了,但他竟又能對自己作為一個背叛者的「轉向」,表示出一股堅定意志,他如是說:
劇中對「老鄭」之角色設定,並沒有打算當成是左翼社會主義者在白色恐怖下,被國家暴力排除的標準範式,只有這樣反而更能表現出官宣「轉型正義」的政治現實,棄左投右;或另一種「轉型正義」的政治現實⸺以新的國族敘事置換為國民黨右翼政權虐殺「臺灣人」的曖眛性歷史。不管是信仰與共同體的忠誠對個體存在產生一定的神聖意義,或對共同體的背叛而導致信仰的喪失,左翼社會主義被歷史賦予了任何一種政治運動都不可能具備的情感(affection)因素,這是我們從二、三〇年代以來的文學、藝術等創作典式中已可以發現到的。然而,我們在《感謝公主》中看到的,卻是一位左翼社會主義者通過「轉向」,反而更為空洞地顯示出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築已然崩潰,不只在今日國家強制下所產生的思想變化只剩一片虛無而已,連自身思想的新方向也盪然無存。「老鄭」這個甚至於現實世界中都已失去意義的老人,似乎變成只會自怨自艾、不斷說著一套套空洞的人生教義,最後我們看到的不過是歷史殘留下一團形消骨蝕的團塊而已。
所以要問的是:《感謝公主》作為一齣被肯定的另類「白恐戲」,它所呈現的「轉型正義」的政治性觀點,如何通過戲劇的形式架構出敘事的結構?首先,導演高俊耀以「戲中戲」的技法,把宋元南戲《朱弁》中〈感謝公主〉一折挪借至現代「白恐戲」中。這在整體的表現形式上,可能產生審美多元化的效果,但也有可能用了意識流交錯而產生混雜。語言在這裡遂成為一種敘事性的策略:首先是南管古典音韻帶來詩詞化的語言表現,並流動著清淨的、敬虔的聖別化,使這種儀式化的語言具有一種洗滌的效果。這正暗合2004年民主進步黨籍陳其南主持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時,所提出之「不只是『審美性』的,而是一種『文化共同體』的重建」9的說法。若接續本文前述關於「想像」的提問,是否可以說:這個神聖的南管,到底為共同體提供了怎樣「想像」(imagined) 的文化人造物?
值得我們關心的問題是:《感謝公主》中具有洗滌效果的古典語言,作為想像的文化人造物服務右翼國族主義,實則為跨時空下的「白恐戲」,提供了一種幻想式的現代語言,而可能進一步與戲中戲做出一定的連結。原本劇中現代語言是用來揭露白色恐怖的國家暴力傷記,以至於歷史記憶的疼痛不僅可以強化語言本身所反映的意識流心理空間,表現情感集中和意象成形的能力;有甚者,更擴充古典與現代,在跨時空的複雜層次上,流露出淨化過的恐怖和憐憫情緒。但,這種意識流的心理空間,在此展現出的卻是一堆虛虛實實的詩句語言。導演企圖從中整合出統一和完整的故事,所以劇中佈滿不少悲歌慢舞、如夢似幻的場面,串連全劇彌散的悲淒氛圍,並以此作為《感謝公主》主要的敘事性語言。
我們看到的,不是朱弁說的「遠望鄉里,舉眼何處是?見許層巒層聳,層巒層聳,盼我家山,各在許白雲邊」;不然就是老鄭說的「我們活在歷史裡面,但歷史找不到我們」,或「讓世界改變你,然後你改變世界⋯⋯讓愛改變你,然後你改變世界」。劇中從迂迥的語言到借用的語言,終至左翼的語言在這裡已然完全喪失,只見屢屢出現跑圓場等意味意識流心理空間的場面,併置於以上一堆空洞的語言之中。這讓我們在劇場中看到的是一個無法產生間離效果的平行世界,而始終找不到一個讓「戲中戲」可以連結的線索。
 窮劇場X江之翠劇場,2023,《感謝公主》彩排攝影。圖/林育全攝影,窮劇場提供
窮劇場X江之翠劇場,2023,《感謝公主》彩排攝影。圖/林育全攝影,窮劇場提供
最後要問的是:一齣「白恐戲」是在什麼意義下,建構這樣「平常過日子是善、搞革命是惡」的道德分立?是的,我們知道這原本是冷戰時期家家戶戶都在持守的一種戒嚴道德;但在解嚴後,它仍然可以被移置作為戲中告密者善惡並存的道德學,讓告密者首先必須認知告密乃至背叛這種鄙屑的行為是正義的,並訓練自己臣服於下,才能對告密這種「戒嚴道德」較諸於懦弱、有害或不純潔,毋寧更相信是勇氣、有用或高貴。
所以,《感謝公主》中告密者的存在狀態,就需要從統治者的道德價值來定位,到後面他所呈現出的一種悲劇英雄似的高貴感,才得以被觀眾感動。然而,這一切與他的左翼信仰無關。若本劇是以告密者這支敘事脈絡,展開對白色恐怖的所謂「轉型正義」做出一個定義,我們繼而想問的是:告密者在對當局告發地下組織,卻犠牲了眾多同志的生命之後,因其良心受譴,而將告發獎金捐予被害家屬,就能以此為救贖,任同志生命犧牲的事蹟,被遺忘於告密者自我生命洗滌之後的昇華嗎?只能說,這恰恰是對加諸革命同志於其身的傷害和卑劣的漠視。《感謝公主》的告密者正把軟弱變為美德,這或許就是「轉型正義」想要告訴我們的吧。這使我想到漢娜・鄂蘭對與納粹統治者合作的猶太人所提出的質問:「為什麼你要協助毀滅同胞?而最終毀掉你自己?」10
終究,《感謝公主》不過是一個平庸落入俗套的故事,甚至是一齣前現代市民社會的家庭悲劇。編導沒有能力賦予告密者「老鄭」一種可觀的悲劇性衝突,反而將他的軟弱無知,以及對同志的出賣,從密告者篡改成為一位具有哀惻力量的悲劇英雄,從而掩蓋了國民黨白色恐怖殺人的罪責。邏輯如此推演下去,「老鄭」對同志的出賣,造成同志犧牲的非正義,是否就可以被沖淡為殺人正義呢?可以說,《感謝公主》在對臺灣左翼歷史完全無知的狀態下,竟而空想創造出了白色恐怖下「老鄭」這個正邪同體的角色,自然就顯示本劇是一齣左翼敘事被抽空化,左翼意識形態被扁平化,而善與惡、好與壞的人性更是被戲劇化的一齣「白恐戲」。
責任編輯:童詠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