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民攝影(Vernacular Photography)過去甚少出現在攝影史的討論中,雖然實際上常民影像佔據自攝影發明後影像生產的大宗,卻因無法進入知識生產體系,諸如美術館、研究機構或學術單位等而消失在歷史論述中。直到1960年代後,「常民攝影」被攝影研究者暨策展人約翰.札戈斯基(John SZARKOWSKI)提出,並在「攝影師之眼」(The Photographer’s Eye,1964)一展中出現在大眾的視野。1 自此,開始有零星針對常民攝影的研究,歐美各地亦出現由公/私機構建立的常民攝影典藏部門或資料館。而另一波針對常民攝影的討論,則匯集於攝影史學家喬佛里.巴沁(Geoffrey BATCHEN)於2000年發表的〈Vernacular Phototgraphies〉2 ,該文重新梳理常民攝影研究價值及其發展可能。隨後,加上過去對常民攝影緩慢但漸進的研究累積,千禧年後除了常民攝影研究外,亦出現將常民影像視為檔案,重新編輯、變造及修改的檔案式創作。本文以常民攝影的歷史著手,首先提出筆者對「Vernacular Photography」一詞的翻譯見解。接著,指出常民攝影如何鬆動典型攝影史的論述框架,並討論幾個不同類型的常民攝影研究案例。最後,回到臺灣,試論臺灣常民攝影研究的現況及其可能。
在中文語境中,目前「Vernacular Photography」尚無翻譯共識或統稱,若是暫且擱置此攝影類型自西方語境進入臺灣(或亞洲)後所出現的意義轉向,或揉合本地特殊社會文化脈絡可能引申的特殊意義,在原先的脈絡中,將「vernacular」用作形容詞時通常泛指各類出自「常民」(ordinary people)的藝術活動或產物。不論是將「vernacular」一詞置於語言、藝術、建築或生物學的脈絡下,皆可發現其共通點在於強調「本土/自然」(native)。另外,在拉丁字源「vernāculus」的解釋中,亦將該詞定義為歸屬於家族、家庭以及本土的(belonging to the household, domestic, native)。而當「vernacular」作為前綴,成為形容並獨立出攝影的單一類別(genre)後,「Vernacular Photography」最大的目的之一旨在區分其與藝術家/從業者所產出之「藝術攝影」(fine art photography),強調影像出自未經訓練的常人之手,並在家庭、商業及政府等非藝術相關場域流轉。而最早開設「Vernacular Photography」研究及典藏部門之一的現代藝術博物館(Museum of Modern Art,簡稱MoMA)將其定義為「一個用以區分藝術攝影,通常由非藝術家出於商業、科學、法醫、政府及個人目的所生產之影像的概括性統稱。其中又以捕捉日常生活為主題的快照(snapshot)為常民攝影的一種主要形式。」3 可以發現,MoMA 亦強調拍攝者的角色區分及影像生產場域的殊異性,並指出影像原服膺於非藝術生產的脈絡下所產製出的影像也被歸類在「Vernacular Photography」的範疇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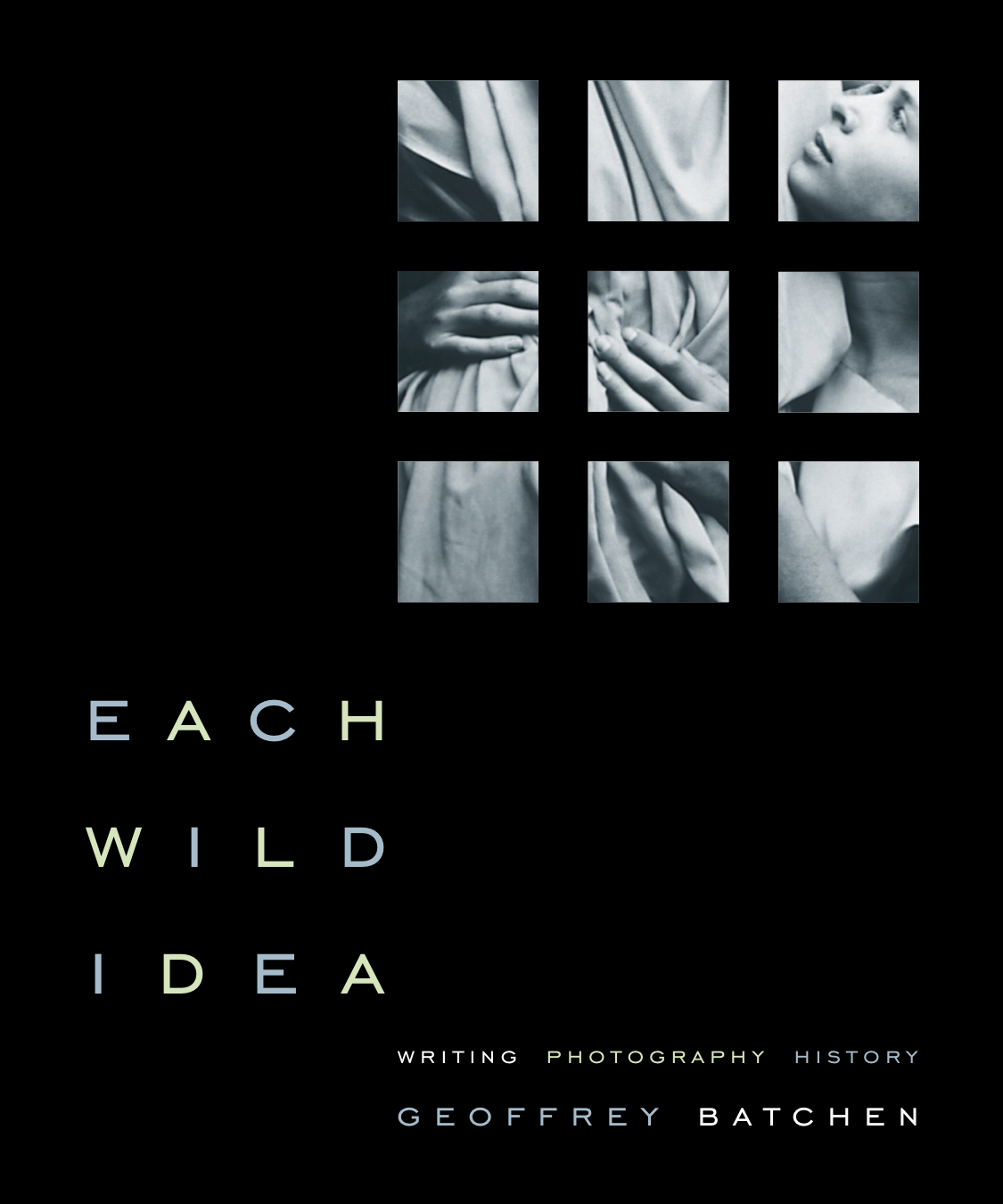 喬佛里.巴沁(Geoffrey BATCHEN)的著作《每一個瘋狂的念頭:書寫、攝影與歷史》(Each Wild Idea: Writing, Photography, History)英文版書封。
喬佛里.巴沁(Geoffrey BATCHEN)的著作《每一個瘋狂的念頭:書寫、攝影與歷史》(Each Wild Idea: Writing, Photography, History)英文版書封。
綜合上述,也許可以將「Vernacular」在攝影類別的語境下翻譯為「常民的」,其所對話的主要對象便是位於光譜另端,經過專業化及理論化後的藝術(fine art)。也就是說,「Vernacular Photography」可以被譯作「常民攝影」,而這時再次檢視 MoMA 對該攝影類別的詮釋中,換言之,「藝術攝影以外的攝影皆可以是常民攝影」,常民一詞在此也被擴張到非常廣大的影像生產領域。這樣巨大的範圍使常民攝影研究不單純停留在攝影(史)研究的範疇內,紐西蘭攝影暨藝術史學家喬佛里.巴沁在其標誌性的攝影研究著作《每一個瘋狂的念頭:書寫、攝影與歷史》(Each Wild Idea: Writing, Photography, History,2001)中,收錄了其2000年初刊於《攝影史》(History of Photography)期刊上的文章〈Vernacular Phototgraphies〉4 ,指出研究常民攝影時需將照片在原先情境下被保存的方式及保存容器一同納入討論,以帶有物質文化(material culture)研究的角度探索過往攝影研究較少討論的影像載體。同時,巴沁認為,過往常民攝影在攝影研究中甚少被關注的其中一個原因在於20世紀後期的攝影史考察與研究大多聚焦在「這一媒介(攝影)的藝術企圖」5。巴沁的說法背後也點出了攝影的媒材發展史。攝影發明之初經歷了一段時間才將自身從「藝術的法庭」中解放,扭轉過往「攝影作為藝術」(photography-as-art)的單一討論方法至「藝術作為攝影」(art-as-photography)中。6
攝影作為一個年輕的媒材面對的不只是自身媒材特性的挑戰與解讀,亦須向外對話已有悠久歷史脈絡的繪畫、雕塑及建築等領域。也因此在20世紀中期,正值攝影努力於藝術場域中站穩腳步的時期,研究者們方興未艾地著手理論化攝影,並建構一種「藝術」的攝影史。而作為難以被理論化,或者說無法快速形成具有脈絡性論述並進入藝術場域的常民攝影,理所當然地被排拒在理論/歷史生產場域之外,而是矛盾地成為佔據世界中影像總數的大宗,卻持續消隱於理論及媒材史中的附屬物(parergon)7。
雖然,所謂藝術的,或者說典型的攝影史 8 佔據了20世紀攝影史書寫的核心位置一段時間,但這樣的媒材歷史書寫終究無法說服研究者。如巴沁文中所提及,在其之前亦有些研究者對攝影正史書寫的選材框架提出質疑,諸如米歇爾.布萊維(Michel BRAIVE)、肯菲爾.威爾斯(Camfield WILLS)及海因茨.海尼施(Heinz HENISH)等人皆打破「典型攝影史」的書寫框架,試圖擴張攝影史書寫中涵蓋的攝影類型。這些對典型攝影史的批判與反省擴增了讀者對攝影這個媒材的想像與認知範圍,但仍未見其將常民攝影當作一個獨立的類別進行研究,亦少見論者以常民攝影為方法試圖影響、補充、甚至改寫攝影史的書寫。直到1990年代後,開始有一些研究者以常民攝影為研究對象,其中家庭相簿便是常民攝影研究中受歡迎的類別之一,舉例來說:攝影研究者莫希妮.錢德拉(Mohini CHANDRA)以斐濟印第安人(Fiji Indian,或稱 Indo-Fijians)的相簿為引,展開斐濟殖民史的考察 9;藝術史暨攝影研究者Julia LUM以加拿大排華時期(exclusion period,1923 – 1967)的華裔移民家庭相簿為研究對象,試圖透過影像論述當時的華人身分及家庭認同問題。10 上述例子及其餘未能於本文提及之家庭相簿研究,大多將常民影像視為個案式的視覺材料(visual material)進行視覺分析,並將影像外延至被景框框選外的廣大社會場域。這種研究取徑雖然未必真的能夠回到攝影史研究的討論中,但常民攝影為研究者打開的――視覺文化式的研究取徑 11――新研究領域,便是鬆動典型攝影史窠臼與缺漏的路徑之一。而上述例子可以被視為一個嶄新的嘗試,她們藉由個案分析輻射至更大的社會場域,展示了常民攝影所蘊含之對話現實與社會的能力。即使這樣的研究依舊未能系統性地對話或反對攝影史論述 12,但它已然揭示這個過去長期被忽略,如今也許無法溯及身分,但真切活在一段社會文化中的雙瞳,它們的目光確實經歷了一段歷史的發展。而研究者所做的努力,便是從歷史的漫天黃沙中尋找隱現其中的目光,掃去塵土,使其重新對焦過去,並成為投射當代的索引。

在攝影發展的180餘年間,它所衍生出的類型及範式不勝枚舉,常民攝影之於攝影研究究竟能夠提供什麼樣的影響?巴沁認為研究常民攝影這類民間藝術(folk art)時不能只將其視為另一個獨立的研究對象,而是透過常民攝影反思「經典化」(canonization)行為背後代表的價值系統。13 透過常民攝影質問典型攝影史,以此切入原先僵固的論述場域及其再現的社會文化,儼然成為常民攝影的研究價值之一。雖巴沁隨後話鋒一轉,將探索異於典型社會文化論述的任務交付給物質文化與被攝影、觀者及作者身分 14 而非(常民)攝影研究,但他同時對影像及其物質載體的雙重考察路徑仍大幅影響著後續的攝影研究者。而在此也許可以進一步討論,構成常民影像背後的意義架構為何?若說典型攝影史使用藝術攝影作為論述對象所缺漏的是藝術生產機構外的廣大社會文化發展歷程,那常民攝影相對於藝術攝影的「常民性」這個層面的歷史意義補完是否全然有效?常民攝影確實沒有理論化的語彙,但當觀者面對常民影像時,如果簡單將其認定為特定脈絡下的社會文化代言人,那麼便錯置了攝影者與社會的互動關係。常民並非純粹的社會文化脈絡生產者,而是不斷斡旋於由眾人構成,但卻同時受到常民無法完全決定/掌握的歷史事件、國家政策、流行文化等一同形塑社會文化的眾多要素的場域中,最終在一個非單向的多股螺旋中逐漸凝鍊成一個念頭,按下快門,常民影像就此誕生。也就是說,常民影像與現實(社會文化)的關係並不能輕易地被劃上等號,但這並不表示常民攝影失去了再現真實的能力,而是當研究者面對常民影像時,應將其視為文化考察的視覺證據之一,以此打開已被歷史封存的社會文化中,尋回彼時的時空語境。
而若是希冀常民攝影真正進入攝影史研究的範疇中,也許首先要做的並非藉此質問典型攝影史的缺失,而是釐清自身希望對話的是什麼樣的歷史?常民攝影的研究問題在於,它並不如藝術攝影具有明確且限縮的類型框架,而是遍佈各種不同範疇的影像生產場域。要將眾多繁雜且殊異的影像統整成一部具脈絡性的歷史幾乎是不可能的,但這不表示常民攝影只能止步於成為視覺文化研究中的視覺材料,而是能夠在清楚界定對話對象的前提下,對典型史觀提出質疑及補充。所以,即使巴沁在文章最後將貫穿全文,「常民攝影作為方法」的起點轉交給物質文化研究領域;也許換個角度來說,他對過往輕忽物質、側重影像本身的攝影研究取向的提醒也可以被轉化為一種典型攝影史研究的擴張之路:研究者考慮的,不再是影像本身的內容(content),而是連帶整合影像與載體,將其視為圖像,捨棄獨尊美學形式的論述傾向,歸還影像的肉身,使影像回到它的棺木中。15 這樣的取徑促使攝影史研究產生新的轉向,使其破除過去過於自信,大寫且獨一的歷史神話,並消除札戈斯基最終僅將常民攝影納入現代主義攝影中過於強調形式與風格的陰影16,讓常民攝影真正進入攝影史研究的討論中,成為參與者,而非失語的旁觀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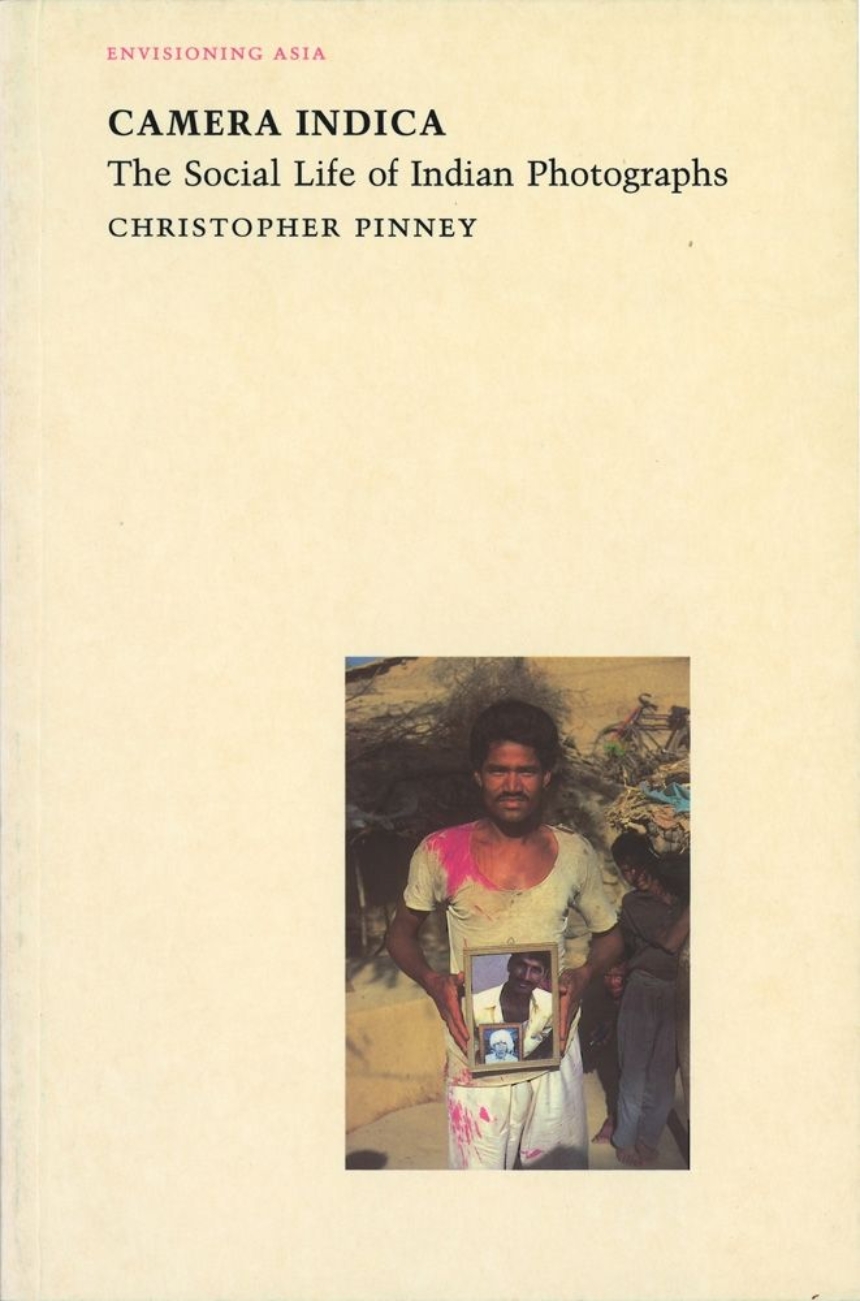 人類學暨視覺文化研究者克里斯托弗.品尼(Christopher PINNEY)的著作《CAMERA INDICA: The Social Life of Indian Photographs》書封。
人類學暨視覺文化研究者克里斯托弗.品尼(Christopher PINNEY)的著作《CAMERA INDICA: The Social Life of Indian Photographs》書封。
同時,若是擴張個案式的討論框架,常民攝影亦能更有效地為斷代史提供一個論述取徑。舉例來說,人類學暨視覺文化研究者克里斯托弗.品尼(Christopher PINNEY)在《CAMERA INDICA: The Social Life of Indian Photographs》(1998)中分別考察了印度受殖民時期的三個肖像攝影實踐轉向,並從影像在不同社會文化脈絡下所產生的特殊意義及大眾對肖像照截然不同的看法,論述了印度社會、歷史及影像三者的特殊關連。或是東南亞文化研究者喬安娜.沃爾法特(Joanna WOLFARTH)以柬埔寨皇室家庭肖像為視覺材料,檢視其中所隱含的國族、宗教、國王三位一體的皇權合法性論述,並藉此梳理柬埔寨皇室與社會文化的互動斷代史。17 在這些看似走向社會與視覺文化,逐漸遠離攝影史的研究中,實際上迸發出了另一種迴返至攝影史討論的路徑:從上一節提及之個案式研究,到前述之更具脈絡並打開具時間尺度的研究,可以發現常民攝影正不斷向典型攝影史提出異議。
攝影的歷史不應該侷限於藝術攝影所顯影出的時間軌跡,在被理論與機構所設定的景框之外,有著無數能夠與其對話,甚至推翻其論斷之可能。典型攝影史切割這些難以被理論化的攝影發展,預先設定的藝術家本位便認定常民攝影至多只能(甚至無法)成為藝術攝影的註腳。先不論若是照著典型攝影史的脈絡討論,這些常民攝影的社會實踐並非完全真空於學院或理論生產場域,而是潛移默化地成為所謂「藝術攝影家」在創作時的考量因素,甚至成為他們意欲對話的對象;形構歷史場域的未曾僅是藝術攝影,而是在交織於社會中的不同驅力、渴望及念頭中,由多種不同領域的攝影實踐者共構而成。歷史場域亦非先於社會誕生,而是在互相指認與參照的過程中生成。常民攝影不應該以加註者的身分進入攝影史的論述場域,而是以自身內含的社會史脈絡,鬆動獨尊藝術攝影或媒材歷史 18 的書寫框架。並從單一/獨立的視覺證據躍升成投射社會文化的銀鏡,介入歷史書寫及論述生成的過程。
 1954年7月1日,臺灣第一次全面換發身分證,規定須有個人照。照片拍攝於1950年代的苗栗頭份鎮,鎮公所為了集中辦理身分證換發作業,請攝影師張阿祥與胡裕祥在戶外為民眾拍攝個人照。圖/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建檔,發佈於《國家文化記憶庫》
1954年7月1日,臺灣第一次全面換發身分證,規定須有個人照。照片拍攝於1950年代的苗栗頭份鎮,鎮公所為了集中辦理身分證換發作業,請攝影師張阿祥與胡裕祥在戶外為民眾拍攝個人照。圖/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建檔,發佈於《國家文化記憶庫》
相對於西方,臺灣攝影史目前仍處於較為前段的建構時期。過去雖有關於臺灣攝影史的書寫嘗試,但大多屬於較為初步的探勘,僅在論述中提出一個線性發展的歷史框架,並在其中置入各歷史時期臺灣(及殖民者)攝影家的攝影實踐。若是從書寫實務層面來說,臺灣攝影史的書寫面臨的不僅是前文提及之典型取徑的缺失,亦有技術面上「攝影如何進入臺灣」的討論,以及進入後可能產生的變體問題;在社會文化面上則有殖民政權更迭對攝影技術的使用與方針問題,以及本土攝影家如何在整個殖民到戰後的脈絡下與非本土攝影實踐對話或互動的關係梳理等。若是暫且擱置常民攝影介入歷史論述的取徑,目前臺灣關於常民攝影的研究較為零散,雖然在不同的影像生產場域皆有少數論著,如家庭相簿方面以藝術史暨攝影研究者許綺玲對臺灣家族照片進行的跨時性書寫 19 為代表;但真正將常民攝影納入攝影史書寫,或予以問題意識化(problematisation)常民攝影,也許除攝影研究者張世倫外別無他人。在《現實的探求――台灣攝影史形構考》中,張氏梳理臺灣戰後初期攝影發展時,提及了「第一個全臺性的攝影事件」,即換發國民身分證,並論述事件隱含的影像監控邏輯。20 身分證肖像照拍攝事件完全不在藝術攝影的脈絡中,相對的,它是一個嵌於歷史背景(白色恐怖)與政治事件脈絡下的產物。影像在此脈絡下所發揮的高度指認特質(idenification)及幾乎降至為零的美學作用,反映影像在特定時期中的特殊使用取徑,而這恰恰是構成臺灣攝影發展脈絡中的其中一個發展分支。隨後張氏便以「俗民」21 影像作為白色恐怖情境下的「創作反例」,指出政治犯劉耀廷在獄中製作的手工相簿,實際上反映了時代語境所產生的特殊情感。從張氏的例子可以發現,常民攝影在特定的影像生成場域中所產生的脈絡大幅影響了研究者的判準,而每一次對常民攝影的考察都像是敞開被凝結的時空,以影像為引,重新賦予已逝的過往動能,驅策歷史論述的多元性,抵達影像與社會互動的交纏制域。

如果說傳統攝影史的書寫是以十分聚焦的眼光劃定一條「藝術的」研究進路,而最終產出的史觀是高度線性且循序漸進的;那麼常民攝影研究便是點亮多盞燈火,試圖以充滿好奇心的姿態打開本是高度流動且交纏反繞的社會文化場域。在不同領域的重疊與互涉中,常民攝影研究使攝影史能夠不只是媒材史,而是與影像製造時未必能被定影,但始終存於背景中的社會文化積極產生對話,並成為一個更接近社會的「攝影(社會)史」。攝影這個與現實有著緊密關係的媒材,不論是在光化學上複現了一瞬的現實,或是在意義上成為了現實的幽魂,皆不可避免地與社會產生關係。透過常民之眼檢視社會中殊異的影像風貌,並不需要將其加以美學化或理論化,而是使攝影更能與現實對話。這也許就是常民攝影自身所能綻放的光芒,及其進入攝影史後所能引發的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