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東尼奧尼
2019年1月,位於倫敦的英國電影協會(British Film Institute)推出義大利名導安東尼奧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生涯回顧影展。名為「以風格對抗現代世界」(Confronting the Modern World with Style)的專題裡,洋洋灑灑列出安氏從第一部劇情長片《愛情編年史》(Cronaca di un amore,1950)到以八旬高齡和溫德斯(Wim Wenders)共導的最後一部劇情片《雲端上的情與慾》(Beyond the Clouds,1995),並羅列諸多罕見短片,堪稱全面完整。片單中一個引人側目的作品,是安東尼奧尼1972年的《中國》(Chung Kuo-Cina)――一部當年曾在國際間引起軒然大波,並在因緣際會下,曾以「變造」方式在臺灣三台電視聯播的紀錄長片。
與工作團隊於北京天安門廣場進行拍攝.jpg) 安東尼奧尼(左)與工作團隊於北京天安門廣場進行拍攝。圖/張世倫提供
安東尼奧尼(左)與工作團隊於北京天安門廣場進行拍攝。圖/張世倫提供
在中國政府與周恩來的懇切邀請、以及義大利公廣頻道RAI的資金協助下,向來具有左翼情懷、同情共產革命的安東尼奧尼,在文革正如火如荼進行的1972年造訪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官方安排主導的八週行程裡,拍攝團隊一路造訪了北京、河南林縣、蘇州、南京、上海等地。以旅途見聞順時組織、長達三個半小時的《中國》一片,以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文革童歌開頭(「我愛北京天安門/天安門上太陽升/偉大領袖毛主席/指引我們向前進」),最終以上海雜耍團融合文革樣板戲與奇觀表演的20多分鐘特技表演作結。如何向西方「展示」中國,中國又該如何「呈現」自身,自始至終一直是這部片子最重要的問題意識。
《中國》裡雖然有許多充滿宣傳色彩的安排場景,安東尼奧尼卻不時游移出中國官方原本的規劃指引,不時將鏡頭私密、迂迴地轉向共產新中國下的小民階級,並以安氏影片一貫的寡言、靜寂與疏離手法,運用長拍鏡頭與稀疏旁白的現代主義美學風格,讓觀眾屏息直視攝影機所捕捉到的社會主義實驗樣貌。
 拍攝過程雖多處受限,但仍對庶民生活多所著墨的《中國》。圖/張世倫提供
拍攝過程雖多處受限,但仍對庶民生活多所著墨的《中國》。圖/張世倫提供
《中國》裡不斷出現的一些拍攝手法,例如攝影鏡頭與被攝者之間長時間的沉默對視、旁白佐助的極簡零星、以及傳統問答訪談形式的揚棄闕如,一方面象徵著西方與東方之間難以逾越的文化隔閡與凝視距離,正如艾柯(Umberto Eco)所言的,安東尼奧尼作為電影版「馬可波羅」文化大使的不可能性,1二方面也正如周蕾(Rey Chow)所言,《中國》一片代表著西方世界對於長期被異國化、神祕化、他者化的「中國」,那持續不斷地、意圖賦予其「可見性」(visibility)觀看慾念的一個現代電影起點,至今仍未停息。2
1972年12月26日,兩小時的精華版《中國》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舉行世界首映,但更大的迴響來自73年1月11日,美國ABC頻道在黃金時段播出了104分鐘的全片選粹,出資拍攝的義大利公廣頻道RAI則將該片分成三部分,1月24日在電視上進行208分鐘完整版的公開播放,反應尚稱良好。但令安東尼奧尼始料未及的是,在影片公映約一年後,中國官方開始一連串的批判攻勢,並刻意將「文攻」《中國》一片的戰場,擴及至國際輿論場域,使得該片成為一個不折不扣的外交事件。
 1973年1月,美國電視週刊上刊登ABC頻道即將播出《中國》的預告。圖/張世倫提供
1973年1月,美國電視週刊上刊登ABC頻道即將播出《中國》的預告。圖/張世倫提供
在將《中國》一片查禁後,1974年1月30日《人民日報》首先以官方評論發表了〈惡毒的用心 卑劣的手法――批判安東尼奧尼拍攝的題為《中國》的反華電影〉,正式為此片進行政治鬥爭層面的言論定調。《人民日報》的評論文章裡,言詞尖銳地稱安東尼奧尼是國際帝國主義侮蔑中國的爪牙,影片裡呈現的貧窮、刻苦、落後與傳統習性――雖然對安氏而言,所欲呈現的其實是克難、簡樸、堅毅與新舊並陳的民眾精神――皆是對社會主義「新中國」建設的醜化汙衊。
對批評者而言,《中國》非但「沒有反映我們偉大祖國的新事物、新氣象、新面貌,而是把大量經過惡意扭曲了的場面和鏡頭集中起來……如果容忍這樣的影片在世界上招搖撞騙,那就等於承認任意侮辱中國人民的反動宣傳是正當的行為……我們要徹底揭露和批判這部影片的反革命實質,回答國際反動派對中國人民的挑戰。這是當前值得人們十分重視的思想和政治戰線上的一場嚴重鬥爭。」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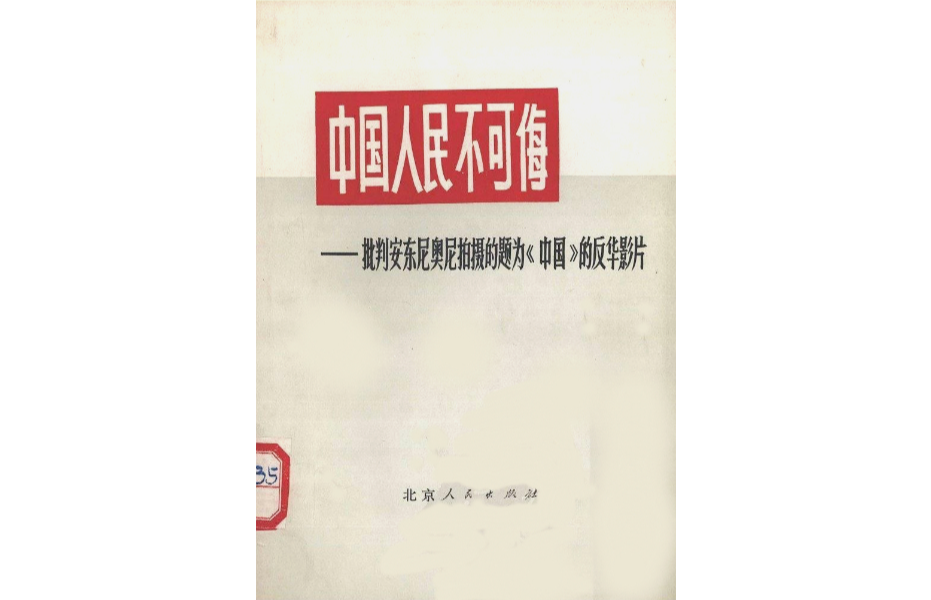 在中共官方鼓動指揮下,諸多出版社爭相刊印了以《中國人民不可侮》為題、內容大同小異的安東尼奧尼批判專書。圖/張世倫提供
在中共官方鼓動指揮下,諸多出版社爭相刊印了以《中國人民不可侮》為題、內容大同小異的安東尼奧尼批判專書。圖/張世倫提供
全國報刊群起批判安東尼奧尼的熱潮,前後持續了一年多,篇幅達12萬字以上。為了強化鬥爭力道,中國官方不但將文章集結為《中國人民不可侮――批判安東尼奧尼的反華電影《中國》文輯》等書,富有對外宣傳任務的外文出版社,更將《人民日報》專文製作成名為《A Vicious Motive, Despicable Tricks: A Criticism of M. Antonioni’s Anti-China Film China》的英文小冊,期能統合並強化海外各地輿論機構與國際外交上的批判力道――原本起於江青四人幫意欲藉《中國》一片批判周恩來的中共內部派系鬥爭,自此逐漸延燒至國際舞臺。
中國當局不但嘗試令瑞典、希臘、法國、德國、奧地利等地禁演此片,此一「反安東尼奧尼」的外交事件並於1974年的威尼斯雙年展達到高峰,激烈的抗爭力道不但使得《中國》從主放映廳La Fenice轉至戒備森嚴的小放映室,安東尼奧尼本人更在映後受到親中人士的連番咒罵。作家艾柯以既同情又嘲諷的語法,描述安東尼奧尼這段經驗:是「懷著愛慕與尊敬之情前往中國的反法西斯藝術家,發現自己竟被指責為受蘇聯修正主義和美國帝國主義雇用,並成為被八億人民所憎恨的法西斯主義藝術家。」4
在一些辯解文章中,安東尼奧尼認為自己從來未曾嘗試去「理解」中國,電影拍攝,終究只是一種「觀看」方式,他試圖用攝影機記錄眼前的人群―― 一個個在社會主義革命後,理論上應該萌生的「新人」及其容顏――而不是進行科學式的政治與社會結構分析。之所以只著重在人群,是因為「每一個人,以其力量進行自己的小革命,這些小革命整體將改變人性。」5
而即便受到中共官方鼓動的猛烈批鬥,安東尼奧尼大體上仍對中國革命抱持著肯定與期待的態度。在一篇名為〈還有可能拍紀錄片嗎?〉(Is It Still Possible to Film a Documentary?)的重要文章裡,安東尼奧尼特意強調,自己並不想找尋某種想像中的中國,而是讓自己沉浸在視覺上所感受的種種真實,「我看到的中國不是童話,而是人類的風景……是這些面孔直侵螢幕而來」。6他並出人意表地引用了魯迅1927年〈無聲的中國〉一文裡,關於何謂「真實」的論說:「真,自然是不容易的。譬如態度,就不容易真,講演時候就不是我的真態度,因為我對朋友、孩子說話時候的態度是不這樣的。……但總可以說些較真的話,發些較真的聲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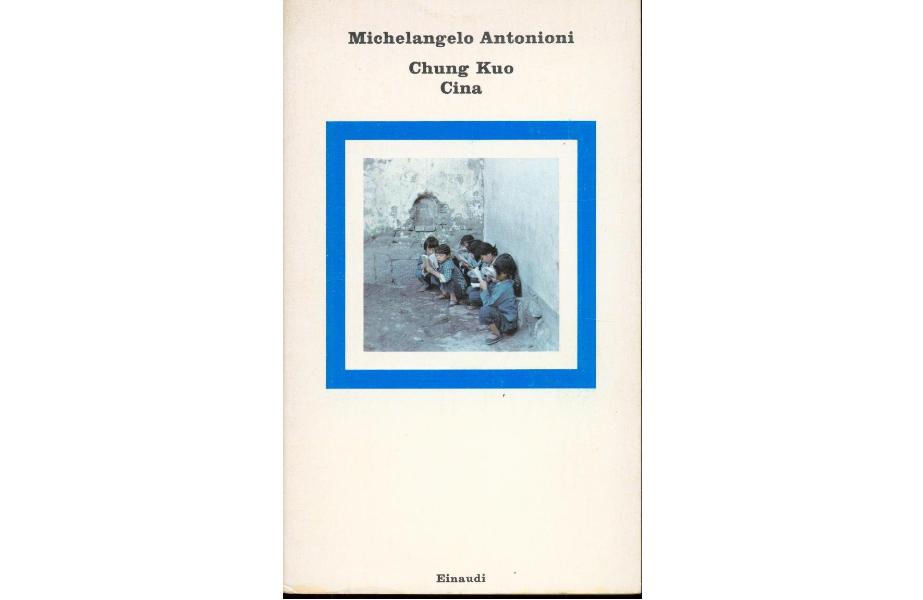 1974年於義大利發行的《中國》專書,包括全片劇本以及安東尼奧尼的論辯文章〈還有可能拍紀錄片嗎?〉。圖/張世倫提供
1974年於義大利發行的《中國》專書,包括全片劇本以及安東尼奧尼的論辯文章〈還有可能拍紀錄片嗎?〉。圖/張世倫提供
安東尼奧尼這種較為幽微複雜的現實主義觀點,在一定程度上肯認了絕對真實的不可企及,以及主觀詮釋的必然性,自然不同於較為素樸直接、接近於反映論的寫實觀點。這樣的真實觀,也顯現在《中國》全片的最後一句旁白:「中國在開放它的大門,但它仍然是一個遙遠的,基本上不為人所知的國度,我們只是看了他一眼。古老的中國有一句諺語,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這句擺在最後的壓軸話語,一方面說明了安東尼奧尼謙虛地自承其作為西方人,實難徹底捕捉到中國及其人民的文化底蘊、精神內涵與完整真實,諷刺的是,他錯誤引用了帶有貶義的「知人知面不知心」,也顯見文化上的誤解錯讀與偏差詮釋,是何其容易以善意為出發點而接連孕生,並成為政治上進行鬥爭的工具。其中一例,便發生在1974年臺灣「海盜版」的《中國》放映事件。
1974年2月22日,臺灣三家無線電視台聯合播出了全長僅一小時、以黑白畫面呈現、影像聲軌重新編輯剪裁,並改寫為中文「反共」旁白的特別節目《安東尼奧尼的「中國」》。這件十分匪夷所思、且明顯違背安東尼奧尼創作本意的影片變造事件,究竟是如何發生的呢?此一臺灣自行炮製、粗暴改作的「海盜版」《中國》,又是用什麼樣的影音手法,將安東尼奧尼原本對文革抱持同情立場、自詡為極簡溫柔的紀錄片文本,移花接木成一部反共八股、鬥性強悍的國府宣傳片?

根據前外交官張超英的回憶錄《宮前町九十番地》一書記述,當年任職於國府駐紐約新聞處、負有收集海外輿情任務的他,在注意到美國電視頻道播放過《中國》,而中共當局開始施壓歐洲各國不得播放此片之際,便經由個人管道聯繫,私自從ABC電視台內部取得一套《中國》拷貝帶,緊急郵寄回臺,提供給與政治思想作戰有關的內政部、國防部、警備總部等單位進行研商討論。在海峽兩岸隔絕敵對了十多年、一切來自「新中國」訊息皆為管控禁忌的戒嚴年代,國府內部結論毫不意外地,是《中國》一片不應在臺灣播放,以免影響民心。但在四人幫明確將《中國》定位為辱華影片,「反安東尼奧尼」漸成國際外交事件之際,並由蔣經國本人示意此事可行下,張超英宣稱經由安東尼奧尼女婿牽線,最終代表政府以五萬美元買下了《中國》一片的在臺播映權。7
即便張超英所言不虛,《中國》在臺灣播放一事,仍有許多可疑可議處。首先,是原本色調偏冷、但仍充滿層次細節的三小時半彩色紀錄長片,在臺播放時竟縮減為一小時的黑白節目,與原貌相差甚遠,當時臺灣相關報導卻統一口徑宣稱,此即為《中國》「不加修剪、以存其真」的原初面貌,顯見此一事件背後政治操作痕跡之深。8
其次,即便臺灣放映的《中國》片源來自ABC頻道播放的近兩小時精華版,仍然有一小時的內容遭到政宣單位的檢查篩選,將這部原本具有旅遊散文風貌的紀錄片傑作,竟改頭換面成不折不扣的反共電影。第三,假設張超英購買播映權一事不假,但仍很難想像合約裡會授與臺灣相關單位如此隨性恣意的剪裁空間,更遑論向來對左翼與文革抱有相當同情態度的安東尼奧尼,不可能會接受自己的作品,竟從「對中國人民及其革命的同情」,變成「今日匪區真像描述」。
在此一可疑可議的脈絡框架下,1974年2月22日在三台聯合播放的《安東尼奧尼的「中國」》,其實可以理解為是臺灣政府所炮製出的一個「官方盜版」(official bootleg)文本,而此一放映事件本身,必須置放在冷戰對峙架構下,兩岸進行話語權鬥爭的歷史情境裡,才能得到充分理解。事實上,自從1971年臺灣退出聯合國,並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中國」的合法代表權後,兩岸間對於誰才是貨真價實「中國」、誰是虛假仿冒「中國」的話語之爭,可說漸趨激烈。
1974年在臺灣三台播放的海盜版《安東尼奧尼的「中國」》,就像一幅被彼時現實政治所框架出的「鏡像」,映射出那真偽不明、內容可疑的「中國」,如何被各路地緣勢力所挪用、變造與爭論――究竟具有正當性的是49年後上台的、共產黨宣稱的「新中國」,還是退守東南島嶼、自詡為反共燈塔的「自由中國」?「官方盜版」這句辭意上自相矛盾的形容詞,從影片文本到政治實體間,雙重映射了國府此時面對「中國」符號的多重困窘、進退失據與自圓其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