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疫情仍肆虐全球的當下,我們不時聽到歐美及世界各國與病毒共存的聲音,預示這是未來的新常態。打過疫苗的民眾等不及要摘掉口罩,回到進餐廳以及酒吧的日子。只因為他們不想再經歷疫情期間的種種「異象」,例如一聽到風聲就趕緊到超市搶購糧食與生活用品,大量地囤積衛生紙與印有消毒字樣的用品。不能出門只好一直上網消磨時間,無法跟親友相聚只好視訊保持聯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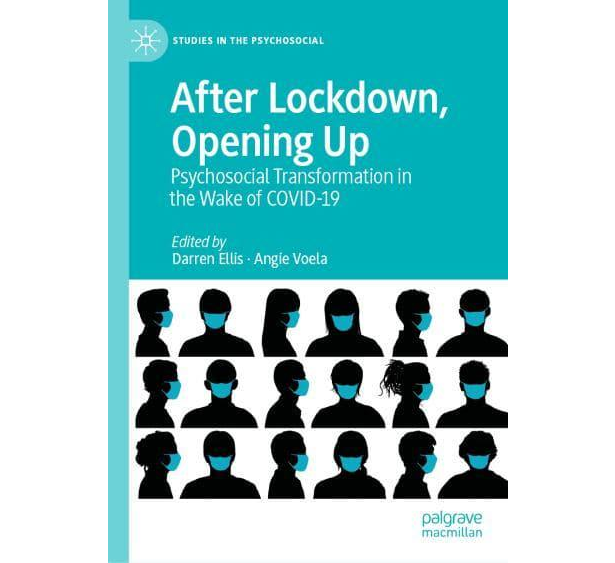 戴倫.艾利斯(Darren ELLIS)與安吉.瓦拉(Angie VOELA)編著的《After Lockdown, Opening Up: Psychologic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Wake of COVID-19》書封。
戴倫.艾利斯(Darren ELLIS)與安吉.瓦拉(Angie VOELA)編著的《After Lockdown, Opening Up: Psychologic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Wake of COVID-19》書封。
英國學者戴倫.艾利斯(Darren ELLIS)與安吉.瓦拉(Angie VOELA)在其編著關於後疫情時代人們精神發生轉變的專書中,精確地描述人們面對疫情爆發以來的封城經驗:大家都好像困在同一條船上,每個人都「待在家,在家教小孩,對於工作以及學業感到焦慮,經歷節節升高死亡率的恐懼,在網路上搜尋相關的事實或是謠言,設計一些例行的活動來保持健康、專注、健美、神智正常,出外卻只能購買生活必需品,什麼東西都想消毒、以及無法出門」。1 這當然不是一條令人愉悅的船,怪不得疫情稍微緩和後,人們就迫不及待地想跳下這艘船往美好新大陸邁進。
在本文我自創「飲食疫象」(pandemic dining scenes)一詞,試圖以微觀的角度探究疫情對人的種種影響,我以「疫象」取代上述的「異象」,就是希望進一步分析原本屬於肺部的病,如何因為人們過度焦慮而影響精神官能,進而讓日常三餐都不得安寧。然而我所謂的疫象並非全然負面,例如疫情也使得人們有大把的時間待在家裡料理三餐,許多人也因此廚藝精進,甚至拍攝自己精心料理的防疫餐,成為疫情期間另類的食景。以下我將以一部英劇作為討論的起點,並輔以去年臺灣三級警戒所發生的軼聞,希望以跨國的視角去分析疫情如何影響我們的(飲食)生活。
英國短劇《隔離日子》(Isolation Stories)的拍攝手法,以現在的眼光來看是相當地陽春,但是當2020年3月底英國不得不決定封城後,不能如常開工的影視業也得跟著社會大眾在家隔離,採用手機與電腦完成四部短篇影集。每一集都以主角的名字作為標題,例如「梅爾」(Mel)、「榮恩與羅素」(Ron & Russell )、「麥克與蘿謝爾」(Mike & Rochelle )以及「凱倫」(Karen ),這四部影集都在演員自家空間完成,算是忠實地記錄英國當時的疫情。
 英國短劇《隔離日子》(Isolation Stories)的第一集主角梅爾(Mel)飾演一位未婚懷孕的女性,在隔離期間所經歷的生活變化。圖 © ITV Studios
英國短劇《隔離日子》(Isolation Stories)的第一集主角梅爾(Mel)飾演一位未婚懷孕的女性,在隔離期間所經歷的生活變化。圖 © ITV Studios
第一集的梅爾是位未婚懷孕的女子,在疫情期間她即將臨盆,引得她的同事與家人頻頻對她表示關心。她雖然表面堅強,但是卻不時地打電話咒罵不支持她生下小孩的前男友,卻因為撥錯電話意外地認識從未碰面的陌生女子,彼此互相鼓勵打氣。第二集則是兒子照顧疑似染疫父親的故事,父親榮恩不斷地質疑小兒子羅素偷他的錢,也因為生病需要隔離心情十分地低落。羅素欺騙榮恩他的鄰居並沒有忘記他,趁英國當時每天下午家家戶戶走出戶外為醫護人員鼓掌的時段,羅素騙父親說這是因為他們在慶祝他的生日才鼓掌。第三集的兩位主角分別是定期向精神科諮商的演員麥克和醫生蘿謝爾,麥克從倫敦到布里斯托工作,卻因為疫情而不得不留在布里斯托,當他前往諮商時已經瀕臨崩潰邊緣。第四集是關於丈夫史蒂芬懷疑妻子凱倫不忠,在疫情期間獨自照顧兩個兒子,卻遇到岳父不時地在家庭院外想探望自己的外孫。史蒂芬最終聽進了岳父的忠告,決定讓妻子跟兩個小孩碰面。
這四集影片分別呈現隔離時大家可以想見的「食景」,例如大腹便便的梅爾,在開線上會議時刻意不開鏡頭,趁機邊開會邊吃東西。要負責照顧生病父親的羅素,因為手邊沒有體溫計,竟然拿油炸溫度計代替。後來發現父親去超市搶購囤了一大堆湯的罐頭(以及一大堆的衛生紙),他乾脆把湯加熱後直接拿去餵疑似確診的父親。而第三集在線上跟蘿謝爾諮商的麥克,中途離開跑去拿外送,當蘿謝爾問他為什麼不將食物拿到鏡頭前吃,他卻說他其實利用外送從倫敦哈洛德百貨買了一罐髮膠,作法十分荒謬。而不知道怎麼跟小孩相處的史蒂芬,只好把小孩都放在廚房裡,看到小孩頭髮太長,竟然異想天開地想拿食物料理剪刀幫孩子剪髮。廚藝不怎麼高明的他,晚餐只烤了片吐司並鋪上豆子罐頭後,就想草草解決一餐。從影片所呈現的食物,以及搞笑地把廚房用品當成醫療用品,其實間接地批判疫情爆發時,口罩、酒精以及醫療用品嚴重不足的問題,而從影片中人們草草地解決一餐的畫面,也引出當時疫情對生活的衝擊。
重新看《隔離日子》,可能會覺得有恍若隔世之感,但是當英國首相也確診後,當時的疫情真的不容樂觀,連英國女王都特意拍攝影片感謝乖乖待在家中的大眾,因為他們此舉能減輕醫療人力已經不足的問題。從飲食的角度去回顧疫情,更能夠看出當時人們必須從單調的(飲食)生活,找到活下去的信念以及把日子過好的理由。
幸好隔離的苦日子等久了還是會過去,英國在當年的8月初因為疫情趨緩,政府推出一個月所謂的 「就餐即幫忙」(Eat Out to Help Out)方案,為了拯救餐廳、咖啡廳以及酒吧之前因為封城而無法經營的困境,並試圖挽回經濟景氣。民眾不再需要透過手機或是電腦才能跟親友相聚,連政府都強烈地鼓勵人們走出家門消費。這曇花一現的方案正好讓我這窮外國人能夠不用太在乎在外用餐的高消費,可以跟朋友們在餐廳一起享用美食。
可能是因為關太久了,外出用餐的人真的比想像中的多很多,而餐廳為了要招攬客人,店內有各種防疫手段。例如實名制,有的店家很前現代地讓顧客手寫個人資訊後才能點餐,有些則很後現代,手機掃碼填完資訊後,連菜單都希望客人直接用手機點閱,服務生只單純地遞送餐點,付錢也希望直接刷卡,不希望跟客人有太多的接觸。
當然塑膠隔板是很常見的,可能也因為有隔板,我發現那種一大群人從大桌上分食的畫面越來越少見,連中式、韓式甚至是印度餐廳,幾乎都是提供一人份的餐點,這樣的設計對單身貴族們相對友善。而比較誇張的,則是在餐廳中用塑膠布隔出一個又一個的小包廂,硬生生地將顧客關在裡面。例如在我所住的社區裡,原本是家庭式的義大利餐廳,因為塑膠布的關係,不再看到一大家子溫馨地用餐,反而是想吃完趕快離開的上班族變多了。
在古色古香的牛津市大街上,我還發現因為店家要符合安全距離,可以進門用餐的人數也大大地減少,他們於是直接把桌椅擺在路上,每桌也保持安全的間隔,有的還會用盆栽區分每間店。而顧客就在路上開心地吃喝,享受夏天的好天氣與難得的餐飲減價時光。而一些比較個性化的咖啡廳,更是善用戶外空間,大大小小的桌椅、可愛的盆栽以及手繪招牌相互錯落地擺在店附近,顧客點完餐後就到這些奇特的座位區等著服務生上餐點,活生生地成為疫情時的活廣告。
但是在這歡愉的用餐情境裡,幾個月前因為封城而死氣沉沉的英國印象,依舊縈繞在我腦袋裡揮之不去。在顧客的喧鬧聲中,我突然想到疫情爆發時,有新加坡學生被當作中國學生,在倫敦街頭被不理性的英國民眾圍毆。我也記得在超市購物時,因為自己不小心沒有按照超市的防疫路線購物,迎面遇上略帶驚恐表情看著我的白種人顧客,這種畫面卻依然發生在號稱「夢幻尖塔之城」的牛津大學城。疫情導致的仇外心態(xenophobia),能夠因為人們有機會回到餐廳用餐就被平息嗎?
 在疫情期間,許多餐館也因應防疫需求,增設了許多隔板或其他的防護措施。圖/潘建維提供
在疫情期間,許多餐館也因應防疫需求,增設了許多隔板或其他的防護措施。圖/潘建維提供
去年國內的三級警戒應該讓大家記憶猶新,雖然晚了一年,臺灣也不得不體驗全球共同經歷的隔離生活。但有別於英劇《隔離日子》演員所呈現的居家生活,我們看到臺灣的電視節目裡每個人依然戴上口罩與面罩,而人們即使在家中跟主播視訊也會戴上口罩,防疫不分室內室外,防疫即是生活。
而最相關的飲食疫象,莫過於三級警戒後為了減低群聚的風險,我們當時必須依照身分證尾數分單、雙號在不同日期到市場去採買,弄錯天數則會被擋在門外。許多餐飲業者為了撐過疫情,開始轉為外賣或是製作冷凍包,並且鼓勵在家防疫的民眾,雖然不能到店享用美食,他們還是可以將外帶餐點盛裝到餐盤上,配上美酒與音樂讓家裡變成餐廳。然而有更多的業者則因為無法繼續營業而不得不歇業,許多名店因此吹熄燈號。

但是疫情也讓無法自行外出採買的長者們變得更為弱勢,在我目前所負責督導的大學社會責任計畫中,三級警戒也讓大學師生們不能進入社區照顧長者。這群長者在疫情前,因為自己獨居,常常會到關懷據點跟其他長者一同用餐。我所認識的學生志工以及據點照服員曾告訴我,如果不刻意到據點跟其他人互動與用餐,這些長者經常隨便打發三餐,甚至會一個便當吃兩餐,衍生營養不良與胃部疾病等問題。
在疫情期間,大學師生除了持續派送餐點給獨居的長者們,並鼓勵他們可以利用視訊的方式,用餐時打開鏡頭跟社區據點的朋友們寒暄,營造出一切都沒有改變的氛圍。但是在疫情前這些長者就不習慣使用視訊,手機與電腦並非他們與其他人最常用的溝通管道。疫情爆發後,他們不懂為什麼要用視訊的方式跟人互動,為什麼要在鏡頭前跟其他人一起吃飯?最後他們乾脆電話一響又跑到據點,嚷嚷著要與志工以及其他長者互動,雖然無心卻成為防疫破口。
雖然不熟悉手機與電腦等數位落差的情況,多花時間教導長者們或許就能改善,但是獨居的長者們卻以最傳統的方式提醒著我們,所有的尖端科技都比不上一顆馬上要見到親友的心。長者們抗拒視訊的舉止,其實也反應他們想要回到他們所習慣的常態生活,回到跟大家聚會的快樂時光。
在《隔離生活》有個畫面特別吸引人:當史蒂芬終於願意讓妻子凱倫回家看兩個小孩,他叫著兩個孩子趕快去廚房,於是小孩們看到背著大包小包的媽媽出現在後院中。但是導演並沒有直接讓凱倫直接進到家中,而是透過落地窗,凱倫與小孩們隔著玻璃互相嘗試摸著對方的手,雖然看起來親密,但是還被玻璃硬生生地隔著。即使母子看起來很快樂,但透過聚焦雙方的手部,導演似乎展示一種莫名的孤獨感。那就是不管視訊有多方便,透過鏡頭所呈現的影像,就如同演員手隔著玻璃一樣,碰觸不到彼此。
從《隔離生活》、我個人在牛津市的飲食經驗,以及照服員口述的長者鏡頭前跟其他人共食的故事,這些零碎的、跨國的「飲食疫象」都告訴著我們,視訊所建構的常態生活,恐怕只是一時權宜之計。當疫情至今仍反反覆覆地在世界升溫,作為外食族的我們最擔心其實是又不能在餐廳裡用餐,「飲食」因此是我們對於疫情最深刻的記憶,同時也是檢驗「新常態」可不可行的指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