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受邀擔任C-LAB「CREATORS創作/研發支持計畫」(簡稱CREATORS計畫)的文字觀察員,負責觀察的創作者與團隊為黃博志與走路草農/藝團(簡稱走路草),這篇文章為將近半年以來的觀察側寫,針對兩組藝術家創作歷程進行描述,並進一步討論關於藝術家創作期程被「計畫書化」的現象。
起初接到「觀察員」這個任務時,我心中立即浮現了許多的疑問。首先,發覺這項書寫任務與藝術家創作幾乎是同步進行的,每個月都需定期就藝術家的進度,給予即時的觀察書寫。再來,最初手上能「依靠」的資料,僅源自藝術家當初投件的計畫書,以及自身對他們過去創作的理解與爬梳。這樣的觀察書寫模式,不像我過去的寫作經驗,例如可能與書寫的對象有著熟識的關係,因此能夠隨時暢談創作進度並隨意給予意見。同時,也因與藝術家創作同步,無法單就已完成的展覽現場作品分析,進而回顧其創作歷程。另外,藝術家的計畫書真能成為創作期程及結果的想像依據嗎?
況且,黃博志與走路草,皆屬於很會「寫」的類型,那麼作為觀察員,我能書寫的是?在滿腦子疑問的狀態下,我先設定觀察書寫與藝術家的創作,兩者在「時間」上能盡量呈現疊合的狀態。觀察者與藝術家兩者的「距離」拿捏,則隨著幾次的聯絡後,了解到他們各自對於創作的想法與規劃,也逐漸有了些默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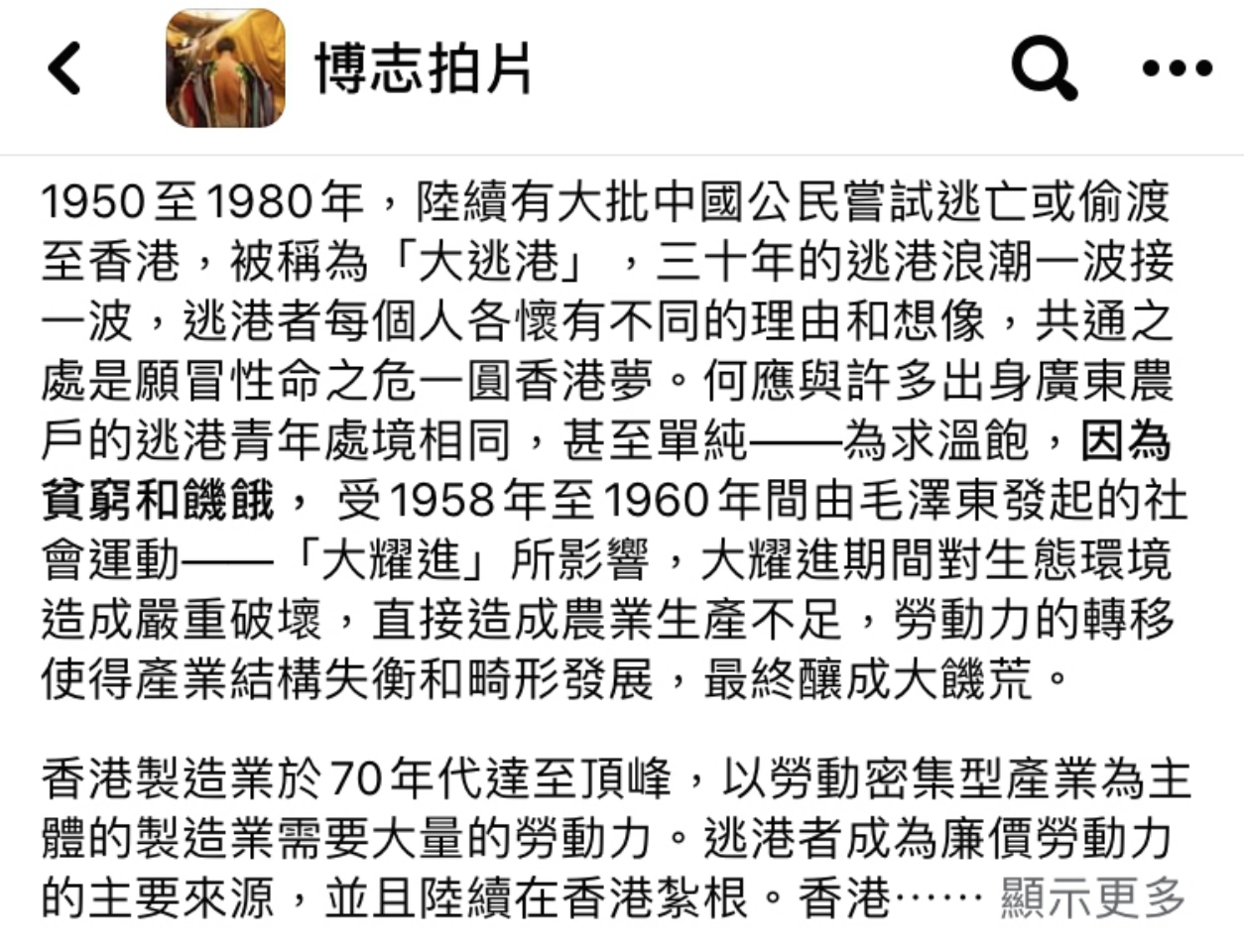 黃博志一段時間會主動在社團裡貼出目前的拍攝計畫進度,故事書寫文字、背景資料整理、場勘圖片等。圖/王瑀節錄提供
黃博志一段時間會主動在社團裡貼出目前的拍攝計畫進度,故事書寫文字、背景資料整理、場勘圖片等。圖/王瑀節錄提供
走路草注重對話,預計以多次面向大眾的展演堆疊;黃博志的錄像計畫,則需要大量的獨自思考,將沉澱後的思緒,轉為文字與影像。因此在這過程中,面對走路草我嘗試將自己變成一名觀眾或一名忠實粉絲,積極參加他們在這段期間的所有展演;面對黃博志,我則保持距離,獨自花費許多時間回顧他過往的創作,以及被動的閱讀他每段時間整理出來的資料與文字,僅幾次主動詢問他進度調整的想法及狀態。
走路草的創作宗旨為「治本於農,以農入藝」,在這次CREATORS進駐計畫――「噥噥時間交換所」中,走路草在C-LAB打造了一個提供對話的場域,在都市分享農村的農忙、農閒的狀態,將農產地與農忙的紀錄帶入,講述農產品生產與醃漬製作等相關知識,將食用的體驗帶入計畫之中。參與者與藝術家從單一食物開始,延伸到食物生產地、製作方法等面向,藉由農產品交流彼此的生活與記憶,連結到產地之地緣脈絡,產生新的關係網絡。
2020年7月時,我對「噥噥時間交換所」的場域想像,是應用C-LAB內的進駐空間,藉由對話的形式,與藝術家、藝術行政、藝文單位、藝術媒體等不同對象,進行的資訊交流練習。但回顧短短五個多月來,「噥噥時間交換所」已從C-LAB的進駐空間與廣場,連接到高雄甲仙的麻竹筍林,並拓展場域至國立臺灣大學植物培育溫室與八德市場。「交換所」並非固定的單一位址,而是在各種場域變形、移動、實踐,不斷強調著各場域之間的生活特性,發展屬於其合適的對話形式,發生不同時空下的「噥噥」。
「噥噥時間交換所」觸及許多單位對象,展開了對話的各種可能性,有同溫層的彼此傾吐、跨域合作的思考、也不忘處理面向大眾的層面。每個場域皆舉辦了展覽與相關活動,邀約其他藝術家共同參展、多次的醃漬及絹印工作坊、不同專業類型的合作展演,表現出藝術如何成為人與人、領域與領域等,看似毫不相關的元素之間的橋梁。
 走路草農/藝團於CREATORS計畫進駐期間透過「噥噥時間交換所」場域想像,開啟與各類參與者的對話。圖/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提供
走路草農/藝團於CREATORS計畫進駐期間透過「噥噥時間交換所」場域想像,開啟與各類參與者的對話。圖/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提供
 走路草農/藝團在都市分享農村的農忙、農閒的狀態,講述農產品生產與醃漬製作等相關知識,將食用的體驗帶入計畫之中。圖/走路草農/藝團提供
走路草農/藝團在都市分享農村的農忙、農閒的狀態,講述農產品生產與醃漬製作等相關知識,將食用的體驗帶入計畫之中。圖/走路草農/藝團提供
《七個在海上的人:賽鴿》源自去年黃博志受「CHAT六廠」委託製作的作品,當時錄像作品完成的部分,其創作靈感來自香港棚仔,「棚仔」可以說是亞洲成衣業的縮影,累積六十多年複雜的歷史、文化與政治構成。
香港深水埗曾以紡織業聞名,由此帶動週邊相關行業,深水埗汝州街布業興盛,成行成市。後因興建地鐵線,1978年政府將布販遷至欽州街。經過幾十年以來,布販自營成了具一定系統的布料市場集中地,俗稱「棚仔」,是舊式小販市集的象徵,其布料源自於大廠商的剩餘零星布料。近年來,「棚仔」面臨政府收地計畫,攤主之一的何應,發起了反棚仔迫遷運動,抗爭背後有著複雜的角力關係。何應原籍為廣東,年輕時為了追尋香港夢,與朋友一行七人偷渡來到香港,偷渡的過程如夢如幻,卻又真實殘酷。
黃博志的創作,長期以龐大的消費體系為背景,分析複雜的產業結構,並深入結構之中的個體,尤其這其中長期被忽略的勞動群體。他改編那些以紡織、製衣業維生的人們的故事,訪談關於他們的「夢」――那些在時代推進及產業演變下被遺忘的生命經驗,各自所懷抱的現實、虛構、夢境般地不同的夢。某種程度下,這些夢都述說著時代潮流下,對於現實的不同想像。而黃博志將受訪者的「夢」、相處當下的對話以及想像書寫成故事,並邀請受訪者參與演出拍攝成影像作品。但拍攝沒有固定腳本,強調現場直覺感受。
黃博志近十年的創作,不單純是議題的討論,或是旁觀地述說他人的生命故事,自己也常轉換不同的身分並身陷其中。他的創作和生命有著緊密難分的狀態,彷彿生命本身就是創作,每個創作計畫彼此牽動,甚至無法有明確的開始與結束。因此,生命中無法預測的變數,例如那些突如其來的病痛死亡,都影響著他的創作狀態與內容。
 黃博志的創作靈感來自香港棚仔,「棚仔」可以說是亞洲成衣業的縮影,累積六十多年複雜的歷史、文化與政治構成。圖/黃博志提供
黃博志的創作靈感來自香港棚仔,「棚仔」可以說是亞洲成衣業的縮影,累積六十多年複雜的歷史、文化與政治構成。圖/黃博志提供
(1)釀酒
第一次與黃博志見面時,我們約在一間十分吵雜的連鎖咖啡廳,身旁那些談笑聲,凸顯我們對話的尷尬感。當天黃博志詳細分享他去年在香港創作的過程,講述何應偷渡香港的真實故事,故事十分荒謬,類似卡繆(Albert Camus)《異鄉人》主角於海邊開的那槍真實而虛幻,他將之編寫成故事:
 黃博志所描述在何應的故事中,何與朋友一行七人,計畫從中國廣東偷渡到香港,為了追尋屬於他們的香港夢,自建了舢舨船。圖/黃博志提供
黃博志所描述在何應的故事中,何與朋友一行七人,計畫從中國廣東偷渡到香港,為了追尋屬於他們的香港夢,自建了舢舨船。圖/黃博志提供
「酸澀草樹」是何應青少年時期的故事,在故事中,他與朋友一行七人,計畫從中國廣東偷渡到香港,為了追尋屬於他們的香港夢。他們每天勤練游泳六小時,閒暇之餘就打零工籌錢,自建舢舨船。一年過後,他們一身輕便地扛起舢舨船,沿著西江而下,從澳門出海。出海不久船身便不敵大浪翻覆,他目睹體力不支力竭而亡的同伴,他說自己也死了好幾次,「一次、兩次、三次……」。最終,他幸運地爬上一座小沙洲島,島上僅有的一棵樹,是貌似在家鄉俗名「酸澀草樹」的植物,他爬上樹,奮力啃食樹上每一片樹葉和果實,隨後睡意侵略他的意識,也偷走夢境,失去時間感的沉睡了,他說:「舒服!」緊接著一天一夜泳渡珠江口,登陸大嶼山,他再次沉睡,但這次,他奪回了他的香港夢。
他的創作需要沉澱他人的生命故事,爬梳整理大量的背景資料,才能轉換成他書寫的一則則故事。
見面的尾聲,黃博志反而跟我聊起創作外關於未來的現實問題,另外我好奇他近期創作轉向的緣由:「你目前確定要做的是錄像計畫,這似乎有別於我對你之前創作的認識?」,他娓娓道來另一個故事:在過去的經驗裡曾發生一名合作對象,在合作過程發生了原本人生以外的可能性,離開家鄉經歷許多展演機會,然而在合作結束後卻不如想像中順利,回到家鄉彷彿一切回到原點甚至後退,當事人請黃博志不要將自身的故事書寫展示,黃博志重新思索自己創作的形式,嘗試另一種想像的可能。
我想起劉天涯書寫的那篇〈黃博志:「我們應該,喝醉。」〉1,「黃博志的藝術作品,似乎都帶著些微醺的氣息,酒,土地,人,盤根交錯,聒噪著、沸騰著,從生命的最深處生長而出。」無論如何,每個生命故事纏繞交錯、錯綜複雜,乘載他人的生命故事似乎就是如此地不簡單吧,好比釀出一杯酒,隨著原料和加工方式的不同,過程及時間相差甚異,沒有所謂標準答案。
(2)醃漬
走路草,我們2019年在高雄認識,當時他們於高雄大社(走路草成員之一陳漢聲的老家)發起「農閒藝術節――大社在這裡」,「農閒」在過去農業社會中解釋為「農事將盡的閒暇」。隨著工業發展下,農業逐漸沒落,許多農村面臨轉型,形成另一種解釋「捨棄農事的轉行」。不同於觀看既有作品的常見觀光模式,走路草將藝術節視為藝術行動,舉辦了一系列活動,試圖與在地居民、外地旅客,有意識地揭露身處之地面臨的轉型、環境等問題,共同思索「農閒」與「大社」之間的新可能性。
 在走路草農/藝團舉辦的「農閒藝術節――大社在這裡」中,韓國藝術家金緣定(Kim Yeon Jeong)的行為表演。圖/走路草農/藝團提供
在走路草農/藝團舉辦的「農閒藝術節――大社在這裡」中,韓國藝術家金緣定(Kim Yeon Jeong)的行為表演。圖/走路草農/藝團提供
當時多數活動都以大社青雲宮為基地,就像是我自己的家鄉,其實沒有所謂村里活動中心,而是將「廟宇」視為社區的社交中心,除了消息放送仰賴廟方廣播系統,選舉投票所也總位於廟埕。參加農閒藝術節的「千元美展――現成物獵人活動」的我,在廟埕從廟公手中領取參賽證明書,並與當地居民一同看著韓國藝術家金緣定(Kim Yeon Jeong)的行為表演,這幅場景有著我小時候,廟口觀看布袋戲的既視感。表演結束後,藝術家用麥克風講述,大社如何使她發想出剛才的表演,劉星佑(走路草成員之一)再以臺語解說給現場的民眾們。當晚藝術家們、參加者們、走路草的家人朋友們一起在陳漢聲老家的透天厝一樓烤肉。
觀察期間,我與走路草一同到甲仙採收麻竹筍,參與採收麻竹筍的任務,不同於平地農作經驗,山坡地的採收除了更費體力,當時又正逢雨季,加上農作物本身的大尺寸,天然環境下泥巴地、坡度皆增加採收的危險度。麻竹筍要新鮮好吃,從砍下那刻才是與時間賽跑的開始,現場馬上進行初步的剝殼處理。雖然麻竹筍比一個成人還高大,但可以留下來食用的部分卻不到三分之一。回到農舍,立即浸泡清水與切片處理,至少得浸泡一夜且不斷換水,才能使嫩筍保持新鮮,去除苦味。勞動後,劉星佑媽媽煮了一桌好菜,我們在屋前圍坐吃飯,侃侃而談彼此家人的近況。
在這兩次的經驗中,我似乎無意地與走路草的原生家庭有所接觸,甚至在甲仙住了一晚,受到劉爸和劉媽的照顧與關心,並得到許多溫暖與鼓勵。走路草的創作實踐就像某種醃漬的過程,單純的農作物經由簡單的調味料,隨著時間的作用,除了延長原料的保存期,味道也更加真誠厚實。
兩組藝術家過往的創作,皆有著從自身家庭延伸出對臺灣特定產業的關注。走路草的兩人,都出身高雄農村,自小隨著父母輩的勞動與對於產業的觀察,看到農業沒落、農村轉型。黃博志在菲律賓服兵役期間與母親往返書信,進而了解母親的人生及職業流變,然而在母親的故事下,所映照出的更是數十年臺灣的變化,和臺灣的社會改革與經濟變遷息息相關。
2020年11月24日我參加了「噥噥時間交換所:八德市場」非公開的VIP場開幕,當中有名為「李淑枝黑膠分享」的活動。李淑枝是走路草成員劉星佑的媽媽(劉媽),在走路草的進駐計畫中,劉爸和劉媽彷彿顧問的角色,提供務農、醃漬等專業技術協助。這次展覽開幕邀請劉媽播放她的黑膠收藏,這些收藏曾被劉媽視為不切實際的過往而扔掉,被劉星佑撿了回來。
劉媽提及國高中時期興趣就是看電影和收集黑膠唱片,她看著手寫的兩大張講稿,緩緩地介紹及播放當天準備的四首珍藏。從第一首歌《海鷗飛處》電影主題曲〈萬沙浪〉,講述瓊瑤電影在當時代給予的愛情想像;第二首歌是由齊豫演唱的〈橄欖樹〉,許多父母輩的共同回憶;到第三、四首由鳳飛飛歌唱的〈奔向彩虹〉與〈心酸酸〉,除了提及心中對女性形象的成形,和待人處事的謙卑態度,更侃侃而談身為父母,如何看待與不捨孩子在藝術上的辛苦和堅持。

關於藝術家母親及其所映照出的時代,那些觸動人心的,是他人的故事,卻也似乎不僅為他人的故事。我們能從這些故事中投射、有所共同感,看到歷史、了解歷史然後發現自己,我想這才是一個地方文化養成所不能或缺的。
2020年底隨著武漢肺炎疫情在臺灣的趨緩,Facebook上出現不少藝文工作者的貼文描述,一是反映年底的結案轟炸、二是關於展覽換檔的速度快於看展的速度,兩者體現某種臺灣藝術展覽氾濫、生產過剩之現象,我不禁反問真的氾濫或過剩嗎?還是這樣的氾濫、過剩思維,其實建立在一期期結果報告與評量的循環下,變形為符合現今多數補助機制的「展示成果」,導致質與量上的展示亂象。
正如王聖閎在〈全球減速及其潛在迷思,一則待解的展覽生產速度學課題〉2一文中所討論的文化加速度,以及對於藝術生產的想像反而被補助、機制給限制。「當代藝術對新展覽和新作的執戀,早已將自身鎖進一個相對狹窄而扁平的生產期程思維裡,忽略了並非所有的創作實踐、作品和文物,都是在相同的時間尺度下創造出來的。」
「先有雞?還是先有蛋?有雞就一定有蛋嗎?」假如將藝術創作計畫書視為雞,而創作計畫比擬為蛋,是先有創作計畫書還是先有創作計畫呢?創作最後一定會有「結果」嗎?沒有在實際過程和計畫書內容相差甚遠的創作計畫嗎?創作計畫有沒有可能中斷到最後無果呢?常聽到「過程比結果更重要」這樣的話,但在現代化社會資訊過於快速的影響下,我們似乎習慣看到結果,或是為了追求結果而前進的方式。然而關於藝術創作的理解呢?生命又該如何被界定與量化?藝術創作期程能完美的「計畫書化」嗎?有了結果就是結束嗎?
2020年11月5號,黃博志的拍攝場勘多數已完成,我傳訊息給他想了解拍片進度,收到四個字的訊息回覆:「天人交戰」,後來的通話中他跟我坦承有著許多的顧慮,例如他拍攝對象的狀態在過程中改變了,假如按原計畫持續拍下去,會導致作品與原本理念背道而馳。在觀察過程中,總能感受到無論黃博志或走路草,皆真誠地面對自己的創作,不管遇到什麼狀況或有無法說服自己的因素,他們會停下思考且不為結果而完成。黃博志表示作品未來會持續,錄像作品會有個結果,但他很肯定不是現在:「時候還沒到吧。」對我而言,這句話真誠到令人動容。
走路草常跟我開玩笑說他們是2020年CREATORS計畫中最低科技的一組,但想想黃博志的創作也何嘗不是,然而如果用實驗研究的角度來看,或許這些生命的故事才是最無法預期,且充滿可能性的,如同具備歷史縱深的釀酒與醃漬技術,必有其動人與超乎科技的存在必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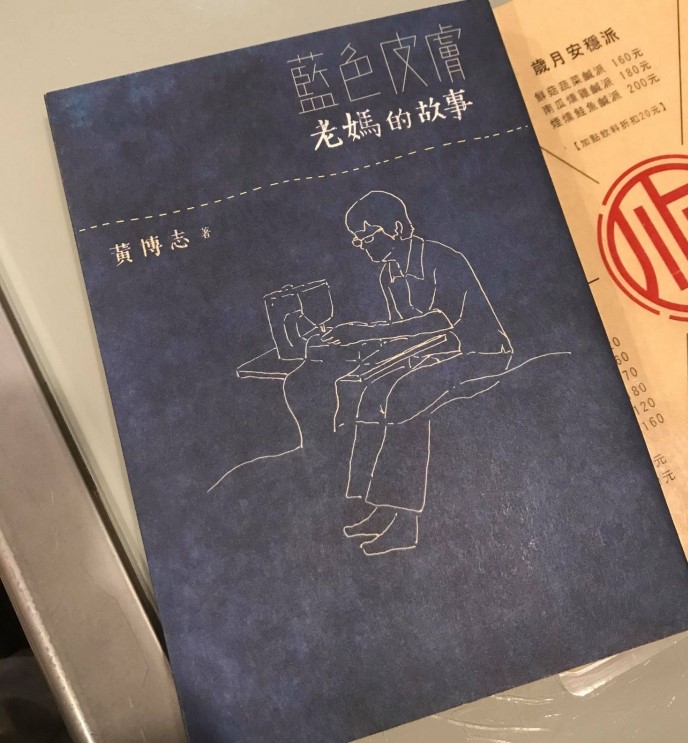 朋友幫我買到了《藍色皮膚:老媽的故事》的實體書。圖/王瑀提供
朋友幫我買到了《藍色皮膚:老媽的故事》的實體書。圖/王瑀提供
或許我有點消極,我並不認為在目前臺灣關於藝術生產有其他更適當的補助機制,因為標準化似乎必然成為某種僵化,但希望作為觀眾,是否能保持開放的態度去看待,當我們對於標準化有著更多想像的可能,這個僵化也能逐漸成為各種形狀。我似乎無法給予關於一個機制該如何的具體建言,但我衷心期望,這樣觀察者的角色有機會成為每一位觀眾的樣貌,當我們有著對於藝術的開闊想像,或者藉由藝術拓展想像的話,或許我們都能好好地直面生活、發現自己。
第一次與黃博志見面時,我想起他的「五百棵檸檬樹」計畫:「檸檬田現在呢?」黃博志有點無奈地笑著說:「持續著,但有的田不得不結束」。後來他在自己的Facebook中也提到:「其實《藍色皮膚:老媽的故事》已經絕版,五百棵檸檬樹死了不少……」
然而,容我稍嫌濫情地說句結尾,《藍色皮膚:老媽的故事》的電子書還買得到,朋友也在淡水的獨立書店架上,幫我買到了已經絕版的實體書,或許創作計畫難以擁有著明確的結束期程,如同一首詩歌、一則故事,只要不失其存在的意義,會持續影響些什麼,並真實地在創作者、在觀者前以某種形式流轉下去……。